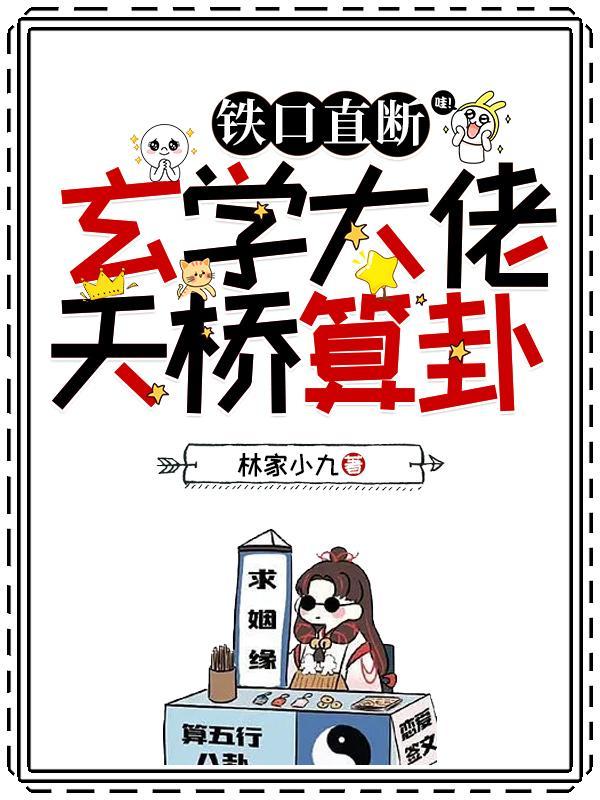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穿回宋朝做经纪人 > 第115章(第1页)
第115章(第1页)
“昔日,妹妹为了上官公子,夜叩上官府门,又骑马几十里地,为上官公子挡箭,可见用情之深。我刚刚不过说了句上官家如今在议婚,妹妹就已经花容失色。尽管言辞倔强,但我想,妹妹不过是在苦苦支撑,既如此,何不再去问问上官公子的心意,也许也未必如妹妹所想的此路不通。”
芷儿的眼泪几乎都要流出来,原来还是有人能看出自己在苦苦支撑。
这十几日,尽管自己因为衣肆的事情日夜忙碌,麻木自己。但,也不是真的就放下了上官玘。
以前,两人每次置气,上官玘总是会率先来求和,自己不理他也好,冷言冷语也罢,上官玘虽然生气,但是最终总是会有些事情,将二人重新拉在一起。
她还是第一次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上官玘。
她想,上官玘大概是真的生气了。
上官家竟然这么快就已经在议亲了,也好,她不是一直希望上官玘“另寻他人”么?现在不是正合她意。想到这里,她泪珠滚落下来。
“姐姐,还烦请姐姐跟白露说一声,我有事先回救济堂。”芷儿哽咽着说完,逃一般的离开了。
芷儿失魂落魄的回了救济堂,只觉得心就像被掏空了似的。
她本来觉得,秦晴如果能在刚开始和许均谈恋爱时,或者两人交往一两年时,就和许均分开,就不会痛苦到失控。她以为秦晴如果早一些发现,就能早一些抽身,少一些伤害。
原来不是。
那种切割掉身体的一部分的感受,再次出现了,芷儿只觉得疼痛不已。
原来,疼痛的多少,并不是总和在一起的时间正相关的。
芷儿现在知道了,即使秦晴在第一次许均遇险、两人第一次彼此交付时就知道许均的“背叛”,也会如她落海那日一样的不顾一切。
这伤心只在于用情多少,不在于时间长短。
没有所谓的长痛不如短痛,痛就是痛。
芷儿一直以“来自香港的现代独立女性”的身份要求自己,告诉自己感情没什么那么重要的,自己不是宋朝女子,不需要有一个对自己好的丈夫才能过活。
没错,她确实不需要丈夫,可是,此刻她却因上官玘要成为别人的丈夫而失魂落魄,悲痛欲绝。
二哥这时因放不下妹妹,也回来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解的问道:“妹妹这是怎么了,刚刚还喜气洋洋,怎么突然就……”
芷儿什么也不肯说,只扑到二哥怀里,尽情的哭泣着。
上官玘这边,如果说以前每次和芷儿的别扭时期,上官玘总是还抱着一丝希望,知道总是会有一些力量将他们重新拉到一起,那这次上官玘就是已经彻底死心了。
他感到愤怒不已——芷儿只因为她苏州那个姓秦的朋友遇人不淑,丢了性命,就将自己也归类为那些心猿意马的男子,以后会抛弃她另娶新欢……
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
他不理解芷儿为什么会将他们的感情看的这么轻,明明自己为芷儿做了这么多,芷儿却因为只别人的遭遇,就将两人的感情视为儿戏。
自从上次救济堂回来,上官玘吐血昏倒,心伤旧痛,一起发作,竟较之前还严重了许多,几乎要了半条命。
只等娶了妻子,和妻子相敬如宾,自己终将会忘记芷儿
等好上官玘不容易恢复,却再不愿提起芷儿。也不肯说原因。
“该不会是现在想娶她的王公大臣多了,就看不上我们玘儿了?”安怀县主揣度道。
“那天的情形来看,感觉这个女子不是这样的人。”上官正细细回忆。
“那是如何?”安怀县主苦恼道。
“难道是因为我们没去赔罪?”上官正对芷儿要求他们去赔罪一事念念不忘。
“我看应该也不是,会不会主要是弟弟自己一厢情愿,毕竟这几个月,我看弟弟每次从救济堂回来,都是可怜兮兮、愁眉苦脸的。会不会人家根本不喜欢他?”
“不喜欢他会为他半夜敲我们的门,又为他挡箭,那些我们都是亲眼所见!”上官正道。
“现在如何是好?”想起过去的种种,安怀县主也不由得着急起来。
“父亲、母亲,让你们担心了。”上官玘沉着脸色,悄无声息的出现在几人身后。
大家面面相觑,一时有些尴尬。
安怀县主先问道:“玘儿,可是因为……”
“母亲,不因为什么,是我和她没有缘分,不想再纠缠了,我已经没了半条命,现在只想简单些,母亲,再去帮我议一门亲事吧。”
是呀,只等娶了妻子,和妻子相敬如宾,自己终将会忘记芷儿。
他下定决心,要彻底和芷儿保持距离。
上官家左思右想,也觉得娶芷儿就未必好,这个女子,个性太强了,眼看自家儿子,这些日子跟没了魂魄似的,这要是再这样来几次,恐怕比那些刀伤箭伤还要可怕。
挑来挑去,便选了安怀县主远在河北的堂妹家的孩子,才16岁。
上官家议亲的事就这样传了出去。
这日,芷儿在码头附近与上官玘擦肩而过,上官玘却像没有看见她一样走了。
芷儿还是头一回见到上官玘对自己如此冷漠,一时竟有些失魂落魄。
“姑娘,何不去找上官公子说清楚呢?”白露惋惜道。
“白露,我不能这样反反复复。而且,真告诉他整个事件,让让他知道了曾在另一个世界害死了我,但自己又完全不记得这回事,这对他而言不也很痛苦吗?”
“那姑娘就任由自己这样伤心吗?”白露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