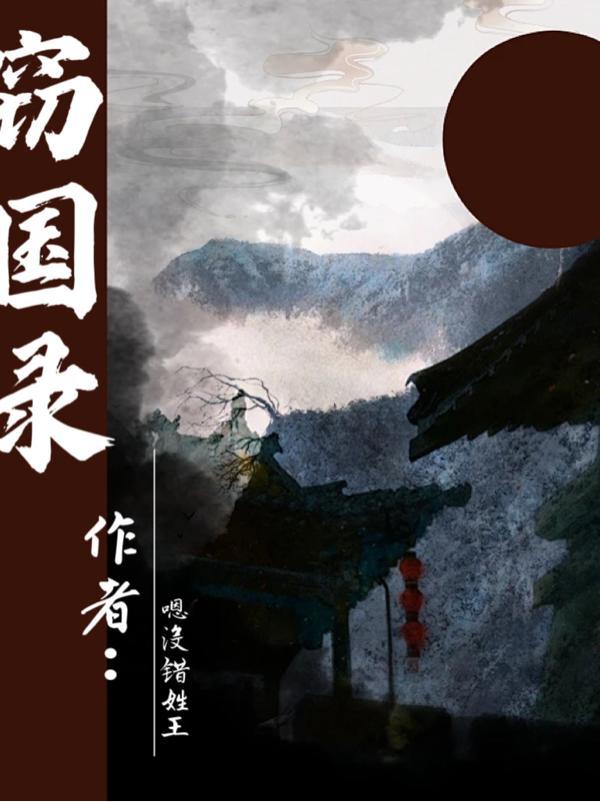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春思乱沐语欢笔趣阁 > 第105章(第1页)
第105章(第1页)
“我表哥今日正好在宫中,你设法找到他,将这封信给他,让他转交给我爹。”
“奴婢这就去。”雪玲也知此事事关重大,应了一声,忙去了。
沈灵薇则深吸口气,忐忑不安地在屋中来回踱步思索着对策,直到又有丫鬟过来催促她过去,她才强行敛住心神,草草吃了些早膳,赶了过去。
然,她本以为此次去得迟了,又要被为首的老嬷嬷狠狠磋磨一番,长长记性。为此,她甚至在来的途中,也暗暗在心里打定了相应的对策,正要付诸行动,却发现为首的老嬷嬷今日竟然不在,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名面善的刘嬷嬷。
沈灵薇一愣,放缓了脚步。
那名叫刘嬷嬷的见到她,忙垂手上前,恭敬地对她道:“李嬷嬷昨日感染了风寒,来不了了,接下来的时日,沈小姐未习完的课业,将由老奴担任教习。”
沈灵薇见状,心头越发狐疑,面上却不显,规规矩矩地给人行礼后,假装诧异问道:“我见嬷嬷面生,之前在哪个宫里服侍的?”
“回沈小姐的话,老奴之前曾是齐王妃的乳母,谢美人入宫之时,王妃怕美人不懂规矩,冲撞了宫中的嫔妃,便将老奴送入宫中,陪伴美人。”
刘嬷嬷不卑不亢地回话,但若细看的话,能窥到她眸底隐着暗暗打量她的神色。
沈灵薇有些不喜,但还是应了声,转过身去正要按规矩站好。
刘嬷嬷已跟上来,伸手将装水的鎏金碗放在她头顶的同时,压低嗓音在她耳边小声道:“少公子担忧您,特令美人将老奴拨过来照料您,小姐待会儿按例走两圈后,便佯装身子不适,剩下的事,交给老奴善后。”
沈灵薇再未想到此人竟是谢璟安插进来的,彻底愣住了。
刘嬷嬷则趁着这个空当,朝后退了几步,众目睽睽之下,拿起桌案上的戒尺,抬起轻压在沈灵薇的肩头,一板一眼地道:“这个肩膀低一些。”
沈灵薇一瞬回神,忙目视前方跟着照做,但剎那间心头阴霾尽散,只余满心欢喜,她不觉翘起唇角,露出个愉悦的笑容来,甚至以往觉得难捱的教习过程,也忽变得轻松惬意起来。
日影西移,万物寂静。
耳边那声声规训的冰冷语调,不觉间渐渐模糊到听不清,宛如天边缓缓移动的纤云,在她脑中慢慢勾勒出那人的清俊的身形,这一刻,她好像有点喜欢上他了。
两日后,在沈灵薇翘首以盼中等来了燕王的回信。
不待雪玲将信递给沈灵薇。
沈灵薇已一把将信夺过去,撕开,一目十行地将信中内容草草看完。
雪玲见她面色渐变凝重,也跟着揪起心弦,忙将信接过去看了眼,不由低叫出声:“圣上病重?宫禁自三殿下出事当日伊始戒备森严?王爷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沈灵薇蹙紧蛾眉,惴惴不安的解释道;“以往圣上只有在真的病危之时,才会下令加强宫中戒备,眼下,圣上还未立太子,如此做,极可能是先稳定前朝和后宫,以免各方势力趁乱夺权,而给他留出足够的准备,册立太子,以及临终托孤筛选辅佐太子的顾命大臣。”
“那岂不是大魏的天要变了?”
“也可以这么说。”沈灵薇说完话,忙走到桌案前,将信放在烛火上烧了。并在心里暗暗地想,最难打的一场仗终于要来了。
思及此,沈灵薇面色凝重地转身问雪玲:“殷文君被关押在何处?”
这些时日,雪玲拿着沈灵薇给她的金豆子,跟撒盐似的偷偷贿赂了不少宫婢,因此获悉了不少消息,“就在侍寝女官后院的柴房锁着。”
沈灵薇闻言换了套丫鬟的服饰,在夜色的掩护下,一路避开宫人朝那边去。
待到地方,雪玲忙给看守殷文君的宫婢每人塞把金豆子,让两人通融一下。
那两个宫婢见状见怪不怪,交代沈灵薇只有一炷香探望时间后,便避到一边去了。
沈灵薇定了定神,推开破旧的房门入内。
挨着墙角坐在枯草堆上的殷文君,手脚皆带着玄铁镣铐,她身上还是前几日穿的那身宫装,此刻,衣襟和衣摆皆有些脏污,她则身形一动不动,头朝后仰,怔怔地望着前方墙壁上巴掌大的窗子,白皙的脸庞上无悲无喜,仿似一座没有感情的雕像。
沈灵薇抬脚走过去,踏踩地上枯草发出的细微声响,令殷文君恍然回神,她转头,看到是她,脸上一瞬闪过阴狠之色,一字一顿道:“你利用我,陷害三殿下。”
沈灵薇见她明明自己已自身难保,可依旧心心念念司亦尘那个负心汉,没由来地想到自己上辈子的事。
那时候她也如殷文君这般被司亦尘外表蒙蔽。
每每司亦尘惹她生气后,回头拿甜言蜜语哄她,她便如飞蛾扑火般无条件地相信他,哪怕他做对不起她的事,她也觉得他一定有不能对外人言的苦衷。
可论起来,也不过是她的一厢情愿。
那时,她父母皆在辽东,她独自一人在京中,祖母又是个爱挑剔的性子,故而,不管她什么,祖母都能挑出她一两处错处,还总打着慈爱的幌子,就连罚她也说是为了她好。
时日久了,她便变得不自信起来,做事也开始畏畏缩缩,再加上和谢璟议婚时惨遭奚落,名声尽毁,放眼京中无人敢娶的境况,两项相加,令她变得极度的自卑和敏感。
而就在那个动荡的时期,是司亦尘主动无微不至地关怀她,也是他,不管她做好事还是坏事,都无条件地纵容她,渐渐地,她被他的“真心”打动,如抓救命稻草般,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懂她,爱她,怜惜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