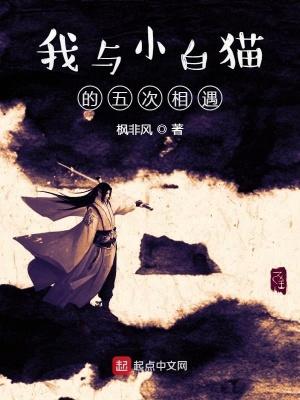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红楼鼎革全文免费阅读 > 第56章 唬朕一跳(第3页)
第56章 唬朕一跳(第3页)
赵文海手忙脚乱的从厚厚的案卷中,拣选出那《精忠报国》的曲词。
永隆帝接过,略扫一眼,神情微变,盯着曲词,眉头蹙起,面露疑惑。
不久,他摇了摇头,目光犀利如刀,厚重的嗓音断然说道:“此曲不是柳湘莲所作!”
“啊?”赵文海轻讶,不知何意,目现茫然之色,这次却不是假装。
永隆帝瞥他一眼,鼻孔轻哼,哼嫌弃道:“文海啊!朕看你这双招子算是白长了!
不然脑子里全是浆糊!你这位子坐不稳当!”
因赵文海非是一般朝臣,而是近臣、旧部,他说话也很随意。
赵文海听出了责备之意,忙跪地谢罪。
他知皇帝驭下严厉,目前倒也不会真拿他怎样,佯作求教实则拍马屁道:“陛下英明神武,聪睿绝伦,臣下自然难及万分之一。只是何以看出不是柳家小儿所作呢?臣着实不解。”
“你把阿谀奉承的心思放在正事儿上,岂会看不出?”
永隆帝微微摇头,也不再计较,与他分析道:“这曲词明明白白写的是‘二十年纵横间谁能相抗’,话虽嚣张,可‘二十年’没必要作假。
十六岁小娃娃哪儿来的二十年?要说这是典故,又是什么典故?朕怎不知?你知道?”
赵文海也觉的有道理,不断点头。此前他只当是寻常曲子,没细想罢了。
忙问:“依陛下看,要不是柳家小儿,又该是何人所作呢?”
永隆帝并没有因臣下查不清反倒问他而生气,继续指点:“由用词来看,情真意切、悲壮雄豪,应是有一番亲身经历。
其中称‘多少手足忠魂埋骨它乡’‘人北望草青黄尘飞扬’,遍观近些年内外之战,当是辽东之役!
作词者当是侥幸不死之人。算他十八岁从军,军中二十年,再加十三年,现在该有五十余岁。
你可知是谁?”
赵文海垂头急思,眼睛忽的一亮,兴冲冲道:“莫非是柳家家奴柳三?”
“那又是谁?”
无名之辈,永隆帝哪里听闻过,卷宗还没来得及细看。
赵文海回忆着案卷资料,说道:“柳三是假名,当年似乎是被权贵之家弄得家破人亡,得了柳棱收留,改名换姓方才活命。
因时间太久,当年的详情未能查出,但此人曾历经战阵无疑。
只是不知他有没有参与辽东之役,毕竟当时柳棱没去。”
“此人有何不妥?”
“那倒没有现。”
永隆帝现在完全不相信他说的,柳棱早死,此前不是锦衣府监察重点,资料有缺在所难免。
命令急促,一日一夜怎么可能调查的清楚?
当即命道:“全部监视起来。”
吩咐完,他放下曲词。
可随即又拿起,反复观看,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凝神细思,方有所悟:以他的阅历和身份,不该轻易被触动情绪才是。
偏偏这短短十二句,竟让他激荡起一腔豪气!
想起此曲最初竟是在私宴上唱出,身为帝王,他也不禁好笑:“‘我愿守土复开疆,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能在满是靡靡之音的宴席上,唱出此等雄歌,这位柳二郎要么是个不解风情的铁憨憨,要么……要么还真是个心怀大志,赤心报国的!”
他当然不会仅凭猜测贸然作出什么重大决定,此事也不急。
正好可以借此看看,能不能钓起一些鱼来。
赵文海凑趣说道:“少年人多些血气,唱此等慷慨之歌也不奇怪。“
永隆帝斜睨于他,目露不屑:“朕看却未必,贾家哪个年轻人有这等血气?柳家年轻一辈哪个有这等血气?心志如何,不分老幼!”
想起往事,他叹道:“柳棱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可惜只知君臣小忠,不知国家大义!不能为朕所用,白白浪费了一身才华!”
赵文海垂头,不敢再接话。
暗思,看陛下态度,应是暂时按兵不动,是要继续钓鱼么?
对了,回去不能忘了收拾柳家那些混账!
……
永隆帝准备钓鱼之时,也有人真的在钓鱼。
乐天郡王府,花园中嘉木葱茏,繁花似锦,山环水绕,真如人间仙境。
奇怪的是此间十分寂寥,内侍和婢女全都不见。
唯独银珑潭畔,雪迟亭下,安静的坐着两个人,正在垂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