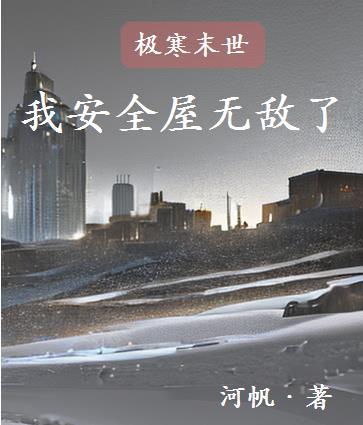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空中楼阁是折射还是反射 > 第83章(第2页)
第83章(第2页)
“你敢。”
哦……她还敢凶他。
“就在这里,可以么?”他又一次很有礼貌地询问她,因为即将要做很不礼貌的事情。
卉满红着眼眸看了他一眼,谢观屏住呼吸,心神荡了下,他没办法,她这样子,会让他更加忍不住。。。。。。
“你那天看到了什么?”
他不知道她在天花板看到了什么,但肯定她得到了某种启发,因为她的思想一下子变得跳脱无法掌控,感触敏锐。
“我不要跟你说。”
“不说?”
谢观继续慢条斯理地摆弄她胸前的系带,这种举止上的优雅比粗暴更危险,卉满心脏有所预警地砰砰狂跳,他居高临下享受她的慌乱与不安。
那双指骨分明的手指上下滑动,最后系了个优雅的风铃花结。
“漂亮么?”
卉满咬牙点头。
“你喜欢,以后给你天天系好不好?”谢观喑哑的声音中有几分乖戾。
“你不是很忙么?”
“是的,我很忙,所以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他看她的眼神陡然变了调,冲突之下有一种蛮荒戏剧性的需求,直接把她扛到楼上,昨天的气还没有出。
她所言是对的,甚至对盖茨比的心情了解准确,对于出身窘迫的男人来说,娶到一个出身名门的白富美代表了他们半只脚踏入了浮华的上流阶级。
他们娶的不是人,只是一份憧憬与象征,奢侈品的象征也大抵如此。
她开始懂男人了,他不想让她懂。
“谢观,你像一只发情的狗!”
卉满被他扛在肩头,用拳头捶他的后背,他吃痛,但不松手,她的话像蛛丝一样缠绕他的心脏,让他动作发狂。
“那你呢?你像什么?狗的发情对象?”
接下来的事情只能粗线条地勾勒,一开始是站着开始的,她不肯,从他腰上滑下来,于是就到了床上,撞击的动作像深刻的五官一样具有侵略性。
男人骨子里的劣根性与征服欲使然,他想听她的声音,想听她喊他的名字,卉满偏不。
她的膝盖跪红了,在这些跟精神攻击比起来微不足道的肉身痛苦刺激下,她那股气性又上来了,小时候调皮被体罚时从来不出声,好像一点都不怕疼,大了有时候却一点委屈就流泪,眼下幼年那种倔劲返璞回来,火一般的自尊炙烤着她。
她咬牙强憋着,浮浮沉沉,缓一会才吐出喘。息,低声泄气。
两人像悖论一样碰撞,卉满精力涣散,可谢观劲头很足,他附在她耳畔,声音懒酥酥,下流又典雅,继续诱使她被深入时说自己的名字,只要说了就会停下。
<ahref=""title="追妻火葬场"target="_blank">追妻火葬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