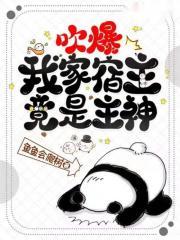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烽火念归人TXT > 第103章(第1页)
第103章(第1页)
第六十章啄木鸟
5月29日李抵达南京,随後就被保释出来。虽说是免职了,但好歹也没真把人关进去。6月的时候李还收到了一枚三等云麾勋章,听闻消息姜培生和婉萍才终於松了口气。7月的时候,婉萍在梨园遇见了个瞎一只眼的老道士,他瞧着婉萍就大步上前,莫名其妙地讲了一句「滩高风浪舟棹破,日暮花残天降霜。」说完转身就走,婉萍愣了几秒,再想找他问清楚,却怎麽也在梨园里找不着人了。这句话具体要怎麽分析?婉萍不清楚,但字里行间里她总觉得不是什麽好事,似是要有灾祸。隐隐的不安持续到了8月,瞎眼老道说的灾还真应验了。「怎麽可能?这不是胡闹呢?」接到电话时姜培生正在家里吃晚饭,他站在客厅惊讶又有些慌张,挂了电话後婉萍问他出了什麽情况,姜培生神色阴沉地摇摇头,直接出门去了警卫司令部。姜培生离开後整整一天都没消息,婉萍想去警卫司令部,但有了上次经验,她也明白自己去了也不过是添麻烦,於是只在家里等他。晚上都是睡在客厅里,想着只要姜培生回来便立刻能知道。就这样等了到隔天的大半夜,婉萍听到咚咚咚的脚步声,她从沙发上坐起来,打开灯看见姜培生一脸疲惫。「怎麽了?」婉萍连忙站起身,从桌上倒了杯水,递给姜培生问:「是出了什麽事吗?」
5月29日李抵达南京,随後就被保释出来。虽说是免职了,但好歹也没真把人关进去。6月的时候李还收到了一枚三等云麾勋章,听闻消息姜培生和婉萍才终於松了口气。
7月的时候,婉萍在梨园遇见了个瞎一只眼的老道士,他瞧着婉萍就大步上前,莫名其妙地讲了一句「滩高风浪舟棹破,日暮花残天降霜。」说完转身就走,婉萍愣了几秒,再想找他问清楚,却怎麽也在梨园里找不着人了。这句话具体要怎麽分析?婉萍不清楚,但字里行间里她总觉得不是什麽好事,似是要有灾祸。
隐隐的不安持续到了8月,瞎眼老道说的灾还真应验了。
「怎麽可能?这不是胡闹呢?」接到电话时姜培生正在家里吃晚饭,他站在客厅惊讶又有些慌张,挂了电话後婉萍问他出了什麽情况,姜培生神色阴沉地摇摇头,直接出门去了警卫司令部。
姜培生离开後整整一天都没消息,婉萍想去警卫司令部,但有了上次经验,她也明白自己去了也不过是添麻烦,於是只在家里等他。晚上都是睡在客厅里,想着只要姜培生回来便立刻能知道。就这样等了到隔天的大半夜,婉萍听到咚咚咚的脚步声,她从沙发上坐起来,打开灯看见姜培生一脸疲惫。
「怎麽了?」婉萍连忙站起身,从桌上倒了杯水,递给姜培生问:「是出了什麽事吗?」
姜培生没接过水,他坐在沙发上沉着脸,好半天后才对婉萍说:「冯明远是个共党。」
从5月份山东事件後,姜培生就一直在说他平日工作得处处小心,万万不能再出其他事情让人抓了把柄,结果才过两个月,居然出这种事!婉萍怎麽想也想不明白,冯明远跟在姜培生身边又不是一年两年,从民国二十八年算起来足有八年的时间了,他怎麽可能会是个共党呢?
「会不会是栽赃呀?」婉萍问。
「你以为我昨天干什麽去了?」姜培生揉着太阳穴:「他们的人反了一个,把冯明远供了出来,保密局顺着线索在他家里查出来还没送出去的情报。人证物证据全,还有什麽能抵赖的吗?我真是怎麽都没想到,这种事情能发生在我身边。我把冯明远当亲兄弟,你知道他把我当什麽吗?」
婉萍摇了摇头。
「说起来真是好笑。」姜培生兀自冷笑了一声,对婉萍说:「他代号叫啄木鸟,我在他那边代称『树』。你别说还挺形象,他那些情报都是从我这儿拿的,可不就是啄木鸟和树吗?我把他当亲兄弟啊,他把我当榆木疙瘩!我前阵子还跟你说张某人是个打呆仗的傻子,好家夥,现在一看我也是个傻子。」
如果按姜培生这说法,冯明远毫无疑问是个薄情寡义之人,把别人一番情谊当牛粪烧。但婉萍记忆里他并非这样,记得有一次姜培生醉得认不了回家的路,是冯明远把人送回来的,背着他上楼时还不断跟婉萍说满哥胃疼,等他醒来了记得去医院看看。而且年初姜培生住院期间,冯明远也时常下班後带象棋过来陪他下棋解闷儿。
「会不会是有其他的意思?」婉萍说:「单就这麽解释,实在太冷情了。」
「还能有什麽意思?」姜培生铁青着脸:「整整八年,到头来我他妈就是个树啊!八年的时间我就是养只猫养条狗,它也不会觉得我是个树,好说歹说也是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你说今天的事情简直是……简直是……这种事我找谁说理去!」
姜培生气得不行,半天再说不出其他话,最後还是婉萍站起身拉住他的手说:「算了算了,你别想了,早点回去睡觉吧。」
「出了这种事情,我就是躺床上也睡不着呀!」姜培生烦躁又无奈地长叹口气。
「睡不着,躺下缓一缓也好。」婉萍拉着人到楼上卧室,姜培生躺在床上一动未动,整夜未眠。第二天天亮,他便离开家里去了警备司令部,在办公室里屁股没坐稳,保密局的人就又找上了门。
「冯明远的嘴很硬,还得请姜司令跟我们再走一趟。」保密局天津站的魏站长说。
「站长亲自来了,那肯定得配合你们工作呀。」姜培生说着站起身,随着魏站长从警备司令部出来,两人坐上车直奔保密局的刑讯室。
此刑讯室在地下一层,大夏天里一早进去照样是一阵阴冷,紧接着钻进鼻腔的就是浓重的血腥味与淡淡的腐臭。
姜培生在这里再次见到了冯明远,他两个眼睛在淌着血,看起来应该是被戳瞎了。手指全部被夹断,胳膊被反捆子在椅子後面,膝盖瞧着也是断了,以诡异的扭曲姿势绑在凳子腿上。
见惯了死人的姜培生看到冯明远这样还是被吓了一跳,他知道保密局的人会上手段,但从未想过是这样的残忍暴虐。一时间姜培生心里涌出两种强烈的情绪,一面是愤怒,恼火於他们这样惨无人道的折磨,如此行径和日本人又有什麽区别?另一面是恐惧,源自於人的本能,面对一个无比熟悉的人变成眼前这副样子,哪怕是久经沙场的也要生出恐惧来。
「满哥,是你吗?」冯明远的声音低微而嘶哑。
「什麽满哥,我在你那不是树吗?」姜培生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了冯明远的对面:「说吧,你在我那窃取了哪些情报?你们在天津的传递点在哪里?你的上下游还有谁?」
「不是的。」冯明远痛苦地摇晃着脑袋,一张嘴姜培生看见他牙齿也被掰掉了好几颗。
「不是什麽?否认你是共党?这边证据充足,你别再狡辩了。」姜培生对冯明远说:「魏站长他们的手段你也见识了,不如今早说,免得再被折腾。」
「满哥,我饿了。」冯明远没有回答姜培生的任何问题,而是对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买一碗面?」
哈?对於这个要求姜培生也是没想到,他侧头看了眼站在一步远的魏站长,说:「别跟我打感情牌。你不啄木鸟吗?吃虫子就行了,吃什麽面呀?要想吃面也简单,你赶紧把该说的事都说清楚。说完了,你要吃什麽面,魏站长都能给你买来。」<="<hr>
哦豁,小夥伴们如果觉得不错,记得收藏网址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