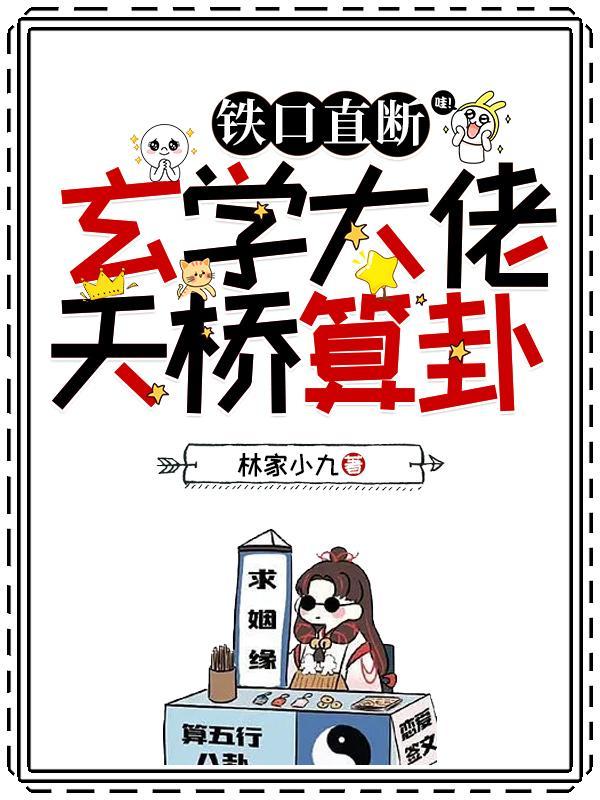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问九卿姒锦全文免费最新章节 > 第120章 借刀(第1页)
第120章 借刀(第1页)
普济寺的夜,向来多雨。
文嘉早早便抱着女儿,蜷缩在禅房的床榻上,睡下了。
禅院的檐马在夜风中晃荡,出清脆的叮咚声,将门外范秉的咆哮也送了进来。
“我要见公主!你算什么东西,给我滚开!”
“滚开——”
“老子可是公主的驸马,当朝的驸马爷范秉!你个秃驴,是不是活腻了!”
“找死吗?”
今儿天未亮透,范秉便寻到了普济里来纠缠。
在晨课钟声里跪求原谅,哭得声泪俱下。
说自己和平乐绝对没有私情,那天在端王府的事儿,是被人陷害的……
在旁人眼里,范驸马在公主面前卑微至极。
从清晨跪到晌午,一直到烈日高悬,见文嘉依旧不为所动,他耐心便消磨殆尽,跪不住了,说了一些尖酸刻薄的话,灰溜溜下了山。
夜幕刚落,普济寺的小僧正要关上寺门,他却拎着酒坛,大摇大摆地闯了进来。
这时候,香客都已散去,寺里僧众都是修行之人,轻易不会动手,范秉借着几分酒意,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肆意撒泼。
一哭二闹三上吊,他比之泼妇尤胜。
文嘉捂着女儿的耳朵,将一个绣着七宝璎珞的护身符,轻轻放在女儿紧紧攥着的小手里,而后缓缓坐起身来。
砰——
范秉便一脚踹开了禅房。
文嘉的眼神,在巨响声里瞬间冷凝。
“别吵着女儿。”她轻声说着,整了整素白的裙裾,为女儿掖好被角,这才走过去,对着门外两个不知所措的小僧,微微躬身行礼。
“劳烦小师父了,你们先去歇息吧,我同他说几句话。”
清官都难断家务事,何况是公主和驸马的纠葛?
两个小僧双手合十行礼,看了范秉一眼,这才退了下去。
“施主有事,便招呼我们。”
范秉满脸怒容,甩了甩肩头的雨水,“哐当”一声,将酒坛摔在地上,抬脚就要往屋里迈。
“让妞妞好生睡觉不行吗?范秉,这是佛门重地!”
文嘉挡在门口。
烛光映照着她清瘦的面庞。
案头抄到一半的《法华经》,被灯光照得煞白。
五岁的妞妞,蜷缩在禅房的蒲草床上,像一只受惊的小鹿。
她的小手紧紧攥着被角,连同母亲给的护身符,一起握在掌心,脊背止不住地颤抖,却始终没有睁开眼睛。
她是醒着的。
在父亲的暴力阴影下,这个过早懂事的孩子,学会了用装睡来保护自己。
“我们出去说。”文嘉轻声道。
范秉哼声,摇摇晃晃地走近,伸手在她脸上捏了一把,嗤笑一声,转身走了出去。
文嘉看着他歪歪斜斜的背影,又回头看了看女儿睁开的眼睛,对视一眼,安慰的一笑,这才迈出门槛,缓缓将门合上。
“我有多少家底,你最清楚不过。”文嘉走到廊下,声音平静得如同这雨夜的禅院。
“这些年,我的嫁妆都被你挥霍一空。你一开口就要十一万两,我上哪儿去给你弄这么多钱?”
范秉坐在廊下,后背靠着圆木柱子,双眼通红,满是醉意。
“你可是公主!你不会进宫去求皇上吗?一个公主就这点本事?早知道你这么窝囊,老子当初就不娶你了!”
文嘉笑,“不是每个公主都像平乐。你当初是怎么娶到我的,你心里不清楚吗?”
一听这话,范秉像被人戳了肺管子。
他看出了文嘉的鄙视和不屑。
那是当朝公主天生的,高高在上的,他一辈子企及不到的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