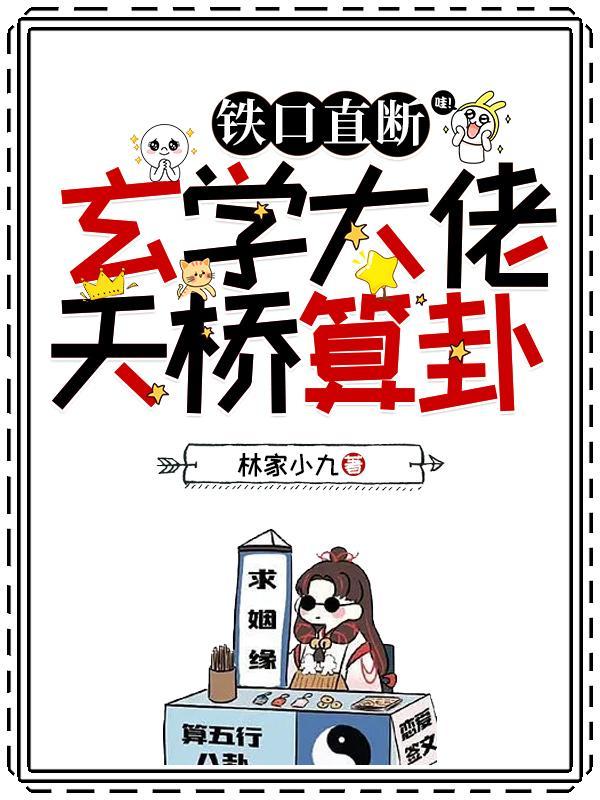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东宫悔免费阅读 > 第101章(第1页)
第101章(第1页)
他都能想明白的道理,殿下却想不明白。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直到叶林走得不见人影了,容玘才起身离开了茶楼。
翌日一早,容玘又来了逸品茶楼,和前一日一样,要了同一间雅间。
这回李泰已不再觉着惊奇,像个寻常茶客般问茶楼的伙计要了茶点,间或提醒容玘用一些茶点,余下的时间只默默站在一旁伺候着,对容玘盯梢叶林的举动只作瞧不见。
如此过了几日,容玘觉着自己理该放心了。
这几日他也算是看出来了,明熙的夫君做事上心,每日早早便来了仁安堂坐诊,到了晚间才关门回去,日日只在家中和仁安堂之间走动,从不在外花天酒地,结交的也尽是一些跟医馆有关的人。
许是家中有孩子要照看,明熙并非每日都来仁安堂,不过若是哪日来仁安堂,那一日她夫君必会陪她一道来,明熙回去时,也是他陪在她身侧护她回家。
明熙的夫君,值得她托付终身。
容玘没再去逸品茶楼,转头吩咐李泰,要他寻个中人赁一栋宅子,旁的没什么讲究,宅子窄些宽敞些都无妨,只一件,须得是楚明熙家对面的宅子,另外中人得是个嘴巴严实的,不可将他们的事到处跟人说。
经过这几日,李泰已对任何事都见怪不怪,立刻就去找了中人,许了中人不少银两,指明要楚明熙对面的那栋宅子,并且要快,最迟这两日就让他们搬进去,又叮嘱中人不许他跟旁人议论他们的事。
中人连连点头应下。
来找他的人大多都会有些要求,今日这位客人的要求不算苛刻,他自没有什么不答应的。何况给的银子又多又爽快,莫说客人要求的不难做到,便是再难办些的,看在银子的份上他也必会将此事办妥。
中人办事利落,不过半日,便找着房东将楚明熙对面的宅子给赁下,容玘他们带的行李又少,只忙活了两个时辰,便将东西收拾妥当了。
宅子不算大,两进的小院儿,跟容玘先前住的宅子完全没法比,不过好歹满足了他的要求,正对着楚明熙住的宅子,打开二楼的窗户朝下看,一眼便能瞧见她宅门前的动静。
李泰看着站在窗前的容玘。
再如何总归比住在客栈里舒坦自在,每日也不必再去逸品茶楼待着。至于旁的,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到时候再寻个合适的机会劝劝殿下了。
容玘这几日仍是差不多同一个样子,日日都在楼上的窗前望着对面,时常能瞧见楚明熙抱着孩子站在宅门前目送她夫君出门,或是留孩子在家中与夫君一道去医馆。
今日一大早,他看到他们一家三口带着石竹坐着马车结伴而行,看他们手中拿着的东西,应是陪孩子去郊外踏青放风筝。
容玘看着这一家子其乐融融的画面,心里委实有点不好受。
每回一想到明熙如今成了旁人的妻子,夜夜躺在那男人的怀里,他胸口就疼得厉害,仿若有人在他的心口上一下下地捅刀子。
可对明熙,他又实在怨不起来。
换作谁是明熙,大抵都宁愿嫁给那个男人的罢。
他留意过叶林,那人是真心待明熙好。明熙跟着那男人,比跟着他幸福多了。
他还记得从前住在南边的时候,明熙特别爱笑,她一笑,眉眼就会跟着弯起,他知她那时候心里是欢喜的。
和他在江州重逢,她几乎从未笑过。
江州的疫情固然是一部分缘由,而另一个缘故,大概就是因为见了他。
早在回京没多久的时候,她便很少再笑,时常还会躲在她的屋子里默默垂泪。
让她痛苦的根源便是他。
而今有她夫君和女儿陪伴在侧,她总会不由自主地露出笑容。她单纯坦率,他知她是真的心里高兴才会如此。
他该替她感到放心的。
她嫁了个良人,总比跟着他要好。
理智上他这样劝自己,可理智和情感,从来就不是同一码事。
他从未如此放不下一个人,明知她不愿见她,还总
是死皮赖脸地主动往她跟前凑。而今知晓她已嫁了人,他仍是对她牵肠挂肚,该做的正事却丢在一旁不去做,偷偷摸摸地看着她跟她的家人进进出出。
惠昭
容玘自认做得隐秘,也的确没让楚明熙和石竹她们瞧出什么不对劲来,唯有叶林察觉到了异常。
回湖州前,叶林有几年一直在外四处游历,因着这个缘故,他比旁人的感知都要敏锐许多。
前些日子他便隐隐察觉到有人在暗中盯着他进出仁安堂,只是那人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从未让他瞧见分毫,是以他只疑心有人在盯梢他,却不知那人是何人。
这两日才消停些,回了家后又开始隐隐有种被人暗中窥探的感觉。
那人应当就躲在附近,倒是没感觉到那人有何恶意。不过无缘无故被人盯着,他心里难免有些不痛快。
家里都是女人,怕吓着她们,叶林便没跟她们提起此事,只装作什么都没发现,每日照旧去仁安堂坐诊,找了个由头劝明熙留在家中照看惠昭。
直到今日早晨,他带着楚明熙、石竹和惠昭一道去郊外放风筝,那人一时躲闪不及,让他瞥见了半张侧脸。
虽只是一瞬,他仍是瞧得分明,那人就是太子殿下容玘。
惊讶过后,他又觉着其实也并不算奇怪。
那日殿下登门拜访,明熙并不曾跟殿下多言,除非殿下自己去寻人打听,否则就当时的情形来看,难保殿下不会将他和明熙还有惠昭误认作是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