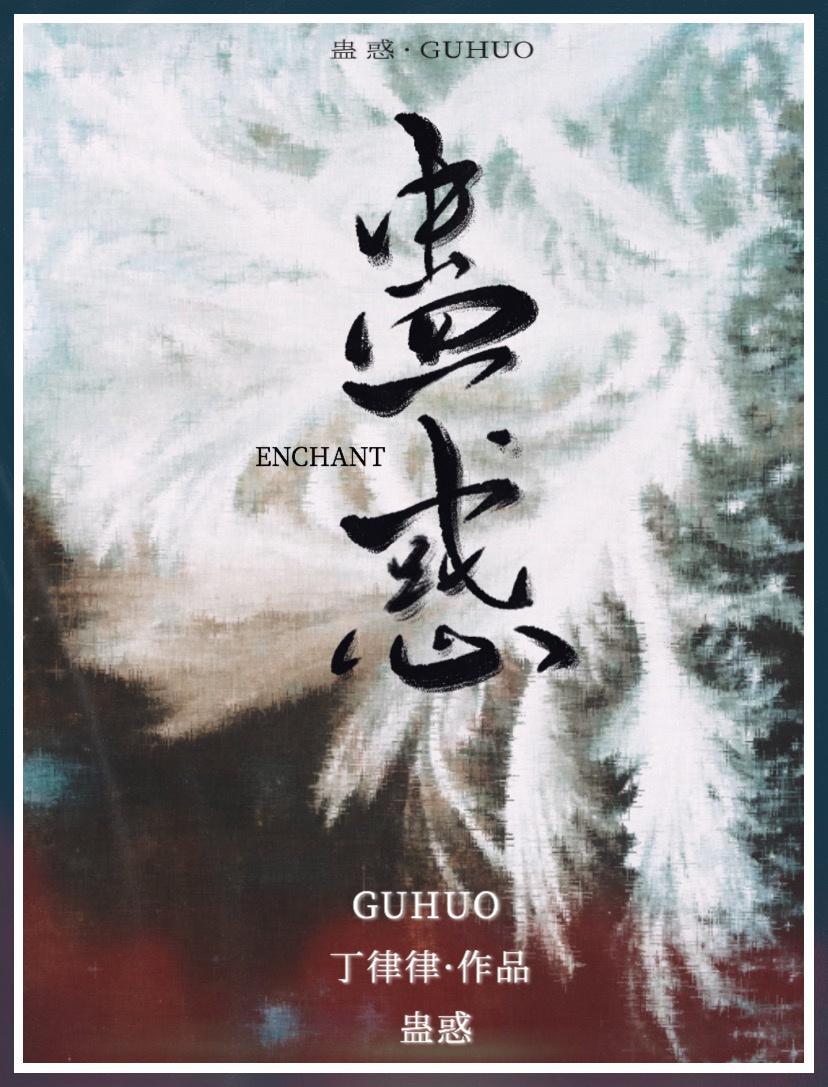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重生后独宠灾星小夫郎22 > 第33章(第3页)
第33章(第3页)
一旁的钟果断道:“那就后日,后日提亲,下旬过门。”
至于廿三还是廿五,到时再商量,不过总之是越早越好。
就连钟春霞也没料到他如此“猴急”,一记隐晦的眼刀丢过来,钟硬着头皮不为所动。
早成亲一日,苏乙就能早一天离了那个家,若不是有礼数拴着,他恨不得现在就直接上门抢亲去,管它三七二十一。
“除此之外倒还有一事,到时需要劳烦婶婶帮忙周全。”
刘兰草不是口口声声说,这些年她从苏乙手里刮去的银钱是为了给小哥儿存嫁妆,既如此,现下也到了该让她往外吐的时候。
七月初六。
寅时末苏乙起了身,往船板上去打水洗了脸。
凉水激去残留的睡意,他烧起陶灶煮了一罐水,又在上面落了个笼屉热米糕。
自上回撕破脸后,虽然还要面对刘兰草一家,但他的心境却变得比以前自在许多。
自己不欠卢家一条命,更不欠卢家一粒米,当一个人意识到过去十几年所谓的“愧疚”,都是外人强加到头上的枷锁,并将其甩掉之后,反而再没什么能让他害怕。
更何况他已不是一个人了。
天色微明时,垫饱肚子的苏乙提着一个装满水的水罐、挎上装针线的竹筐,背篓里塞上虾网等物什,大包小包地下了船。
他近些日子都是如此,除了睡觉、吃饭,几乎不在卢家船上停留,免得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相看两生厌。
寻了处僻静的礁石上坐定,他借着晨光从竹筐里拿出一个快做完的褡裢,继续做起来。
褡裢是一种布口袋,一般前后两个兜,刚好能挂在肩头,容量比腰间的荷包大,而且不占手。
上回给钟补衣裳时,苏乙注意到钟肩膀上磨得有些厉害,应当是扁担所致。
而且对方每次去乡里卖鱼获进项多,铜板一堆,寻常荷包装不下,揣怀里鼓鼓囊囊不好看,放在筐里又怕贼惦记,还是褡裢更合用些。
他为此拆了一件自己的衣裳做褡裢,布料有些旧了,遂合了两层做底,现在只差往上缝口袋。
按理说哥儿送汉子的东西多多少少都会绣些花样,一来是好看,也可借花样传递心意,二来是显示自己手巧。
可惜绣花需先有花样子,以前苏乙给卢家人做针线时都是用的刘兰草攒的花样,现在他没法去要,也没有徒手画花样的本事,只能尽力把褡裢做得结实,好让钟能用得久些,弥补不那么好看的缺憾。
想到钟,苏乙出了会儿神。
自雨天过后,这两三日两人未曾见过,钟好像很忙,或许就是在忙提亲的事?
想及此处,他拈着针埋下头,觉得心跳都乱了。
关于对方具体哪日上门提亲他也并不知晓,他独来独往,连个能打听消息的人都没有,当然小哥儿自己去打听这等消息好像也不太妥当。
他红着脸继续缝针,加两个裁好的口袋并不难,只是为了让走线整齐,针脚好看,他刻意放慢了度。
忙活完后天已大亮,褡裢完成,他翻来覆去地检查一看,自觉没什么错处,满意地叠整齐放回竹筐,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和肩膀。
看日头已经过了辰时,如果钟今天不忙别的,要去崖壁附近下海的话,这会儿应该已经快来了。
苏乙含着隐秘的期待,盼着他今天能来,这样自己就能送出褡裢,下回钟去乡里时,指不定就能用上了。
“哎呦,乙哥儿你怎在这里,快回你舅家船上去,一大伙子人可等你好半天哩!”
一道声音突兀地响起,苏乙扭到一半的脖子骤然拧回来,害他听见“咔嚓”一声。
他有些紧张地看去,见来人是王家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