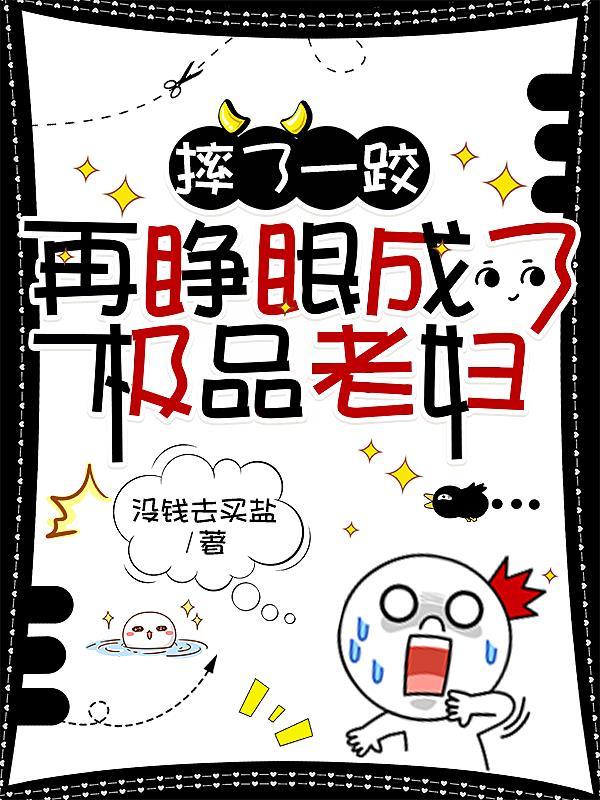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深眠主动恋与深空 > 第24頁(第1页)
第24頁(第1页)
「我不標記你。」袁醒垂眸看他。
「真、真的?」方眠眼睛微微一亮。
袁醒低頭靠在他肩上,低低喘息,道:「用信息素安撫我。」
要安撫一個a1pha,除了標記,另一個辦法就是釋放信息素。如果對方基因契合度高,僅僅憑藉信息素的氣味,也能安撫一個陷入易感期的暴躁a1pha。可問題是,方眠穿越至今,不僅沒有遭遇過情熱期,而且根本就不知道怎麼釋放信息素。事實上,直到今天,他也不知道自己信息素的味道是什麼樣的。
「我真的不會啊。」方眠哭喪著臉,「要不你去雪地里滾一滾?」
袁醒抿著唇,手指微微按壓方眠的頸後,腺體正常,可就是毫無反應。他嘆了一聲,說:「張嘴。」
「啊?」方眠一愣,「要幹嘛?」
說話間,已經張了嘴。袁醒捻著他的下巴,低頭吻住他的嘴唇。方眠眸子一縮,幾乎成了針尖那樣細。心臟狂跳了起來,耳朵漲得通紅,滿臉不可思議。
和女孩兒都沒有拉過小手親過嘴的他,被一個男人給親了!
嘴唇被碾磨著,對方甚至撬開了他的嘴唇,溫熱的舌游進了他的唇瓣之間。方眠下意識死死咬著牙關,不讓袁醒更進一步。
袁醒額上的冷汗更多了,微微和方眠分開,道:「你的體液有信息素成分,要麼這樣安撫我,要麼被我標記。」
方眠又嘗試掙扎了一下,袁醒的眸子一豎,蛇眸盯獵物似的把他盯住,冷冰冰的。方眠狠狠打了個寒戰,不敢亂動了。
被親,總比被標記好。
就當被狗啃了。
方眠顫顫巍巍地閉上眼,嘴唇微微張開。牙關鬆了,袁醒長驅直入,吮吸他的舌尖。冷杉木的味道不僅充盈鼻尖,更進到了口腔里,仿佛要一路直下,沁透肺腑。一面親吻,一面引著他的手撫摸。方眠手一抖,驚恐地睜開眼。袁醒在他唇邊呢喃:「幫我。」
方眠渾身僵硬,不肯動。
袁醒頓了頓,嗓音低沉,略帶威脅,「要標記你麼?」
方眠抖了一下,終究是愛惜貞操,默默順從他的指引。這樣遠比被標記強吧!被蛇啃脖子,想想就很可怕啊。大丈夫能屈能伸,方眠一鼓作氣,閉著眼完工。
屋裡的冷杉香味更濃了。
「謝謝你,阿眠,」袁醒低聲說,「你做得很好。」
從前只能打抑制劑、隔離,獨自忍受痛苦,現在他真的被方眠安撫了。和以往強行壓下易感期的高燒不止不同,這回他通體舒暢,沒有任何不適。
方眠拍開他的手,手忙腳亂下了床,拿了張紙巾仔細擦手。
「你快走,不要待在我這裡。」方眠斬釘截鐵道,「我不可能和你結婚。」
袁醒,不,穆靜南淡聲道:「蕭擇對你圖謀不軌,留在這裡,你會被他占有。」
他說得對。左右為男,前後夾基,該如何是好?方眠抓著自己黑灰色的頭髮,欲哭無淚,「可惡啊,你們這些基佬能不能放過我!」
穆靜南靜靜望著他,「你要做選擇,選他,還是選我。」
這傢伙嘴上說給他選擇,可冷酷的眼眸里根本沒有要放他走的意思。詭計多端的基佬,慣會騙人,方眠早就看透他們了!正思索著怎麼逃出生天,忽然,粲白的光照進窗戶,昏昧的屋子裡頓時亮如白晝。外面響起車子的引擎聲,還有沉重的軍靴踏著地面的響聲。
有人用大喇叭沖屋裡喊:「穆靜南,束手就擒吧。我們是保衛軍,你已經無路可逃!」
方眠愣了,「臥槽?」
保衛軍怎麼會發現穆靜南在這裡!?
他偷偷摸到牆邊,悄咪咪地窺探窗外。只見他們家的院牆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被拆了,剛才穆靜南和他太激烈,居然沒有注意到外面的動靜。黑壓壓的反叛軍包圍了房子,密密麻麻的槍口全部指著他們的方向。許多輛車堵在原本是圍牆的位置,大燈全部打到最亮,晃得方眠眼睛疼。
要瘋了,他是無辜的啊!能不能放他走再抓穆靜南啊?
穆靜南穿好衣服,站起身,向方眠伸出手。這男人身材高挑,一身黑衣,挺拔如松。因著極高的個子,氣質極具壓迫感。
「選我麼?」他居高臨下地問。
和易感期的a1pha待在一起,無異於自曝菊花。方眠重重拍了下他的手,「我誰都不選!你幹嘛?你要出去投降?」
穆靜南長眉一壓,眸色清冷,「穆家的軍人,寧戰死,不投降。」
所以這是要出去硬剛?方眠兩眼一黑,「要不你去剛吧,我精神上鼓勵你。」
穆靜南默默看了他一會兒,拉著他的手腕拽他起來,不由分說,推開門走了出去。方眠被他攥著手,仿佛是被蛇咬住了的獵物,根本掙脫不得。就這樣,房門打開,光潮湧來,穆靜南避也不避,帶著方眠朝那幫嚴陣以待的保衛軍而去。靴子踩在雪裡,橐橐作響,片刻後他們站在了夜空之下,所有人視線的中心。
被那麼多槍指著,冷風還颼颼往衣領里灌,方眠緊張得肚子疼。穆靜南卻面無表情,神色不改,一身凜冽的殺伐氣,這架勢仿佛不是保衛軍的通緝犯,而是檢閱軍隊的君王。
蕭擇立在保衛軍後面,遙遙望著他們。
「不要傷到方眠。」他低聲對保衛軍說。
保衛軍的士兵再次拿起喇叭,喊道:「放開人質,穆靜南,束手就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