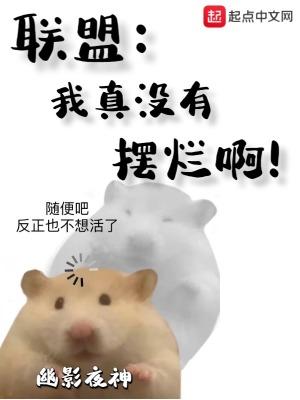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蒙尘珠子 > 第31頁(第1页)
第31頁(第1页)
正快活著被人一腳從雲端踢回地面,屠夫火冒三丈,舉起地上豬肉筐里的大砍刀就要朝那多管閒事的人砍去,那把尤帶豬血的砍刀快要掄到那人肩頭,珠碧終於回過神來,一句小心脫口而出,而後才發覺自己杞人憂天,他身上似有一層看不見摸不著的屏障,那鋒利剔骨大砍刀沒碰著他一根頭髮,就見一縷極淡的金光裹挾刀身,瞬間——七零八碎。
只餘一根光禿禿的木頭刀柄還在屠夫手裡握著。屠夫驚掉了下巴,看看手裡光禿禿的刀柄,又看看面前人,頓時傻了。
仙人瞅都不瞅他一眼,淡淡道:「自己滾,還是我送你?」
「你……你究竟是甚麼東西?」
仙人不語,那屠夫哆哆嗦嗦地拉起褲子,顫抖的手怎麼也系不住褲帶,好半天才連滾帶爬地撿起自己的豬肉筐,一步三回頭,狼狽地沿著紫竹小道逃走了。
已昏沉的天地之間,只剩下他們二人了。
珠碧這才白著一張臉去弄身上凌亂的衣裳,可衣裳被撕得和碎布條沒甚麼兩樣,堪堪就掛在身上,擺弄來擺弄去也遮不住身體。
正躊躇間那仙人走進一步,替他將桌上披風拾起,溫柔地替他圍上了。
仙人丹唇輕啟,清泠的語調不摻任何七情六慾,仿若九霄鶴鳴,清透悠遠:「沒事了,別怕。」
珠碧聽聞,如吃了仙丹一般,渾身都輕飄飄的,像躺在一片鴻羽之上,在雲中飄飄蕩蕩,分不清東南西北。
怔怔地對著他澄澈的眼眸,放任自己陷入這一片溫柔里。
從未有過的感覺蔓延全身,只是單單望著他,珠碧就快要醉了。
他是如此,可眼前人的眼睛裡卻是一片空空,沒有情沒有欲,甚麼都沒有。
珠碧難以自控地被他幽深如墟海的雙眸吸引著,三魂七魄都似要被吸進去。
風月場中美艷勾魂的珠碧,拼盡了力氣練出那一身勾引男人的本事,才叫男人們為他神魂顛倒。而這人只憑一雙眼就把閱盡男色的自己弄成了這副魂不守舍的模樣。
他做這一行,見過無數的男人,沒有哪個人男人看到自己的身體還能毫無波瀾。
珠碧幾乎是堅定了,他並非凡人。
凡人受六欲七情所困,要到兩眼空空的境地,實在是不大可能。
仙人見他似是魘住了,半晌動也不動,便先開口:「天色暗了,山中不安全,快些回去罷。」
珠碧呆呆地啊一聲,才將三魂歸位,半晌方才呆呆道一句:「多謝。」
仙人憑風而來,沒有一點預兆地闖入他生命中,如今風又起,似乎下一刻,他又要乘風而去。
思及此,珠碧幾乎是不假思索地,拉住他半幅袍袖,那衣袖觸手滑軟冰涼,似一朵仙雲輕又軟。
半幅衣袖忽然被拉住,仙人低頭瞧,珠碧仿佛是自言自語:「聽說山上的薔薇花開了。」
一句不著邊際的話,聽得仙人不明所以。
珠碧垂眸低喃:「天寒地凍地,薔薇花怎麼會開呢……寺里的小和尚告訴我,是有神仙下凡了。」
仙人淡淡道:「你想說甚麼?」
起初珠碧是半個字都沒相信。可那莫名其妙碎成七八片的刀,那憑空出現的金光,那雙清澈純粹到極致的眼睛,容不得珠碧不信。
他抬眼看他:「你就是那個神仙,是麼?」
既然是神仙,又為甚麼要下凡?凡間有甚麼好,骯髒虛偽黑暗可笑,珠碧對這世間恨之入骨。
被看穿了身份,仙人沒甚麼好辯解的:「別說見過我。凡人之事,六欲七情牽扯甚多,我原不該插手。」
珠碧輕笑,對上他的雙眼,語調如春日消融的雪水,清透柔軟:「可你還是救我了。」
他是三靈共修之靈鷲帝君,與靈樞、靈修二位本為一體,乃天地太清之氣幻化,是自鴻蒙初辟時就存在的創世神,生來不通七情不曉六欲。
存在於三界的日子如恆河沙數,到底活了多久他自己早就算不清了。只是每日觀望著參橫斗轉,過一天是一天。
他原不願沾染凡塵俗世間的紛亂糾葛,想來是做神仙與生俱來的高傲,他又總是閉關,萬八千年獨對一片虛無的澹淵玄境,無上聖潔。便見不得眼前這堆肉體橫陳、汁液橫飛的場景,污了佛門聖地,污了自己一雙眼。
那渾身橫肉的屠夫,骯髒齷齪,滿口粗葷,實在是教人倒胃口。在這人間少有的清淨之地也敢如此猥瑣,帝君無法容忍,遂才出手制止。
若不是弄丟了佛友的珠子,他豈會放著清淨的神仙日子不過,巴巴地跑下凡來?
靈鷲拂袖輕嘆:「僅此一次而已,離開,莫再糾纏。」
珠碧乍一被他拂開,生怕他乘風而去,又緊緊抓住他的手,道:「你救了我,就是我的恩人,我對恩人向來是以身相許,你不要我糾纏,就不該招惹我。」
可靈鷲豈會受制於凡人呢?他輕飄飄向後掠了一步,珠碧分明緊緊抓著他的手,一瞬間卻憑空消失了,怔怔地盯著他,他淡淡丟下一句:「隨便你。」就消失在了風裡。
徒留珠碧一人在寒風中形單影隻,看著他離去的地方空悵惘。
不過,他也不是甚麼都沒留住,攤開手掌,那串瑩白的玉佛珠靜靜躺在手上,珠碧一笑,如沐春風。他細細端詳手中佛珠,圓潤無暇,溫潤通透。只不過串聯得有些稀疏,似是少了一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