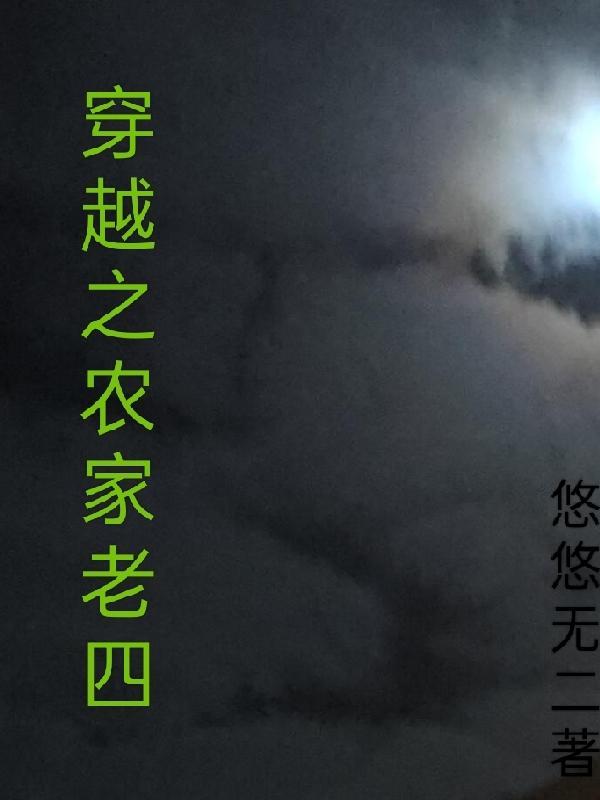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君卧高台 我栖春山 > 第三百五十九章 妒恨(第1页)
第三百五十九章 妒恨(第1页)
陆温眉目疏淡,语气也轻描淡写:“冤有头,债有主,谁羞辱的你,你就恨谁,别将气撒我身上。”
福子站起身,裹着氅衣,冷冷的剜了她一眼:“燕王府的高枝儿,我一定要攀上,不成功,便成仁。”
毅然决绝,不留一丝余地。
说罢,她拔腿离去。
陆温叹了叹,没了氅衣,凉寒之气自然而然的渗透进了她的肌肤,激起阵阵寒粟,她转头,便见天地间又落起了雪。
原是一朵雪白的琼花,滚落进了她的颈侧。
不知为何,她心中空空的,久久立于檐下,瞧着庭院里的冬樱,被厚厚的霜雪所覆盖。
一只雪白的鹰隼盘旋在高空,羽翅一拂,凛冽的冬风刮过一排排冬樱,粉艳艳的花瓣与洁白的雪粒子,在空中缓缓坠落,融入一地清白。
最后,那点潋滟的花色,也被朦胧的积雪全数掩盖。
不留尘埃。
他缓缓踏出房门,举着柄天青色玉柄纸伞,替她遮去雪势,另一手将厚绒斗篷披在了她的肩头:
“送出府去,好不好?”
陆温垂下睫,默然不语。
昨日林玉致见了她,第一句话,便是将灵台府婚宴之事,清清楚楚,原原本本的告诉她了。
劝她三思而后行,劝她思虑斟酌,她如此,无疑是给自己留了个隐患。
看她花样百出,接近自己的夫,说自己的心头,始终淡然无波,是假的。
可她每每想要做出决定时,又会想起,同样的雪夜。
一个柔弱的女人,撑着她,扶着她,一点点站起来,将她背在身后,从雪窟里带了出来。
她至今都记得那轻柔灵动的乡野小调,似夏日的煦阳,一点点照入她的心底,将冷冬的雪意,缓缓融化。
她从不后悔要了她的性命。
可每次夜深人静之时,她都会想起那两颗山药豆的味道。
寡淡如泥,还微微萦绕着湿潮的霉气。
她一时默然,不知如何劝解他,更不知如何劝解自己,最后只能握着他的手,轻声说:
“我想……她如果愿意接受谢蔓这个名字,就是愿意放下了,再……给她一点时间吧。”
谢行湛哼了一声,似有忿怨:“还以为你已经大度到,真的要将我拱手送人了。”
陆温低眉敛目,当真思索起此计是否可行了。
谢行湛瞧她没接话,反而是低着头,蹙着眉头,一副苦苦思索的样子,当即就怒了,恨恨的扯了扯她的袖袍,望着她,眸底似有严冬之意:
“我就随便说说,你莫非真想将我送给旁人?”
陆温抬起头,直视着谢行湛,无波无澜:“就算我愿意,你愿意么?”
他心头沉闷无比,在释放怒意与扮可怜之间,纠结了好几个来回,最后面色悲愤,眸中水光盈盈:
“你若不要我,我就是撞墙,抹脖子,上吊,也绝不会从了她人。”
是意料之中的答案,也是她如此有恃无恐的因素之一。
“那不就是了。”
陆温笑了笑,牵过他的手,拉着他往房内走,揶揄着说:“刚刚立了契,就想着纳妾的话,我可不依。”
“那你还……还……”谢行湛好生委屈,“还允她穿着你的衣裳,占了你的妆台。”
陆温叹了叹:“我似乎也没有更好的法子开解她了,若换作是你,你可有法子解开她的心结?”
二人进了寝卧,他顿住脚步,忽然低声道:“我不会开解她,只会……”
他停顿半许,眼底掠过一丝沁雪之意,幽幽凉凉道:
“杀了她。”
她记忆中的他,万不是这般嗜血好杀的。
陆温蹙着眉:“你对她的敌意,是否有些太大了?”
![我得了圣母病[快穿]](/img/5472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