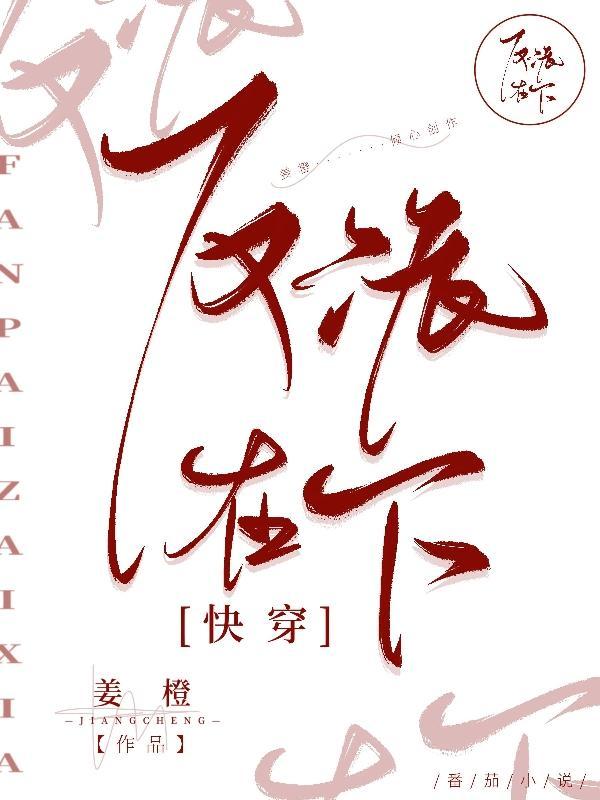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夫君别闹免费阅读 > 第85章(第1页)
第85章(第1页)
袁瑛挪到他身边,他贴在她的耳边说:“寿数谁也说不准呐,我幼时得了一场小小的风寒都险些没活过?来,太医也曾说,我恐怕活不过?二十,自?小就?拿流水一般的补药养着,可?这样薄弱的身子做什么都艰难,倘若真的英年早逝,我也只有?认命。”
袁瑛听得一阵伤感?,忙安慰他:“殿下要?乐观一些啊,人?心情好,才有?精气神,就?不容易生病。”
李瞻眉眼一弯,“你说的对,如果你嫁给我,我一高兴,说不定可?以活得久一点。”
袁瑛脸一红,他轻轻握住她的手腕,说:“若是实在运气不好死得早,你可?以给我殉葬,我们生死相?依。”
泛红的脸颊突然就?变白了几分,袁瑛后背发毛,惊恐地要?抽回自?己的手,“我看殿下你身强力壮,且有?的活呢,殉葬什么的想?得太远了。殿下你你你……先松开我!”
李瞻攥着她的手腕晃了晃,“你愿不愿意呢?”
“我该回家了,殿下你快放开我!”
李瞻看着袁瑛吓得跟炸了毛的小猫一般,笑得一脸愉悦,一抬头,不知什么时候顾逍来了,两臂环胸倚在门口,冷漠的脸上隐隐透着一丝无语。
李瞻这才松开了手,得以解脱的袁瑛赶紧跟他拉开距离,哼了一声,坐回了对面。
“何事?”李瞻抿了口茶,一本正经地看向顾逍。
顾逍走过?来,弯下腰在他耳边说:“昨夜有?一身份不明之人?自?西城门入城,经查探,可?以确定是太后的安排。那人?入城后便消失了踪迹,我已经让人?去?找了。”
李瞻神色稍冷,“嗯”了一声。
等顾逍出去?,袁瑛问:“殿下,出什么事了吗?”
李瞻眉目间的霜寒化开,对她一笑:“无事。”
她坐在窗口,伸着脖子一脸好奇地往楼下看,见顾逍正翻身上马,“他就?是宣宁伯吗?听说他戍卫边境,战功赫赫,今日一见,真是英姿勃勃呢。”
“那种武将都是粗人?,不懂得怜香惜玉的。”李瞻关上了窗户,“茶都要?吹凉了,快喝吧。”
……
另一边,黎又蘅等了半晌也不见沈徽音到来,在屋子里待着头晕脑胀的,便开了窗户想?要?透透气,却瞧见楼下的一个眼熟的面孔,正是沈徽音的夫君。
他们夫妇俩是一起出来的吗?黎又蘅想?问问沈徽音,开口喊人?:“王……不是,那个张……”
她竟忘了沈徽音的夫君叫什么。眼见人?家都要?走了,她出了屋子,脚步匆匆地下楼去?。
走得太快,在楼梯上还不慎撞到一个男人?。她仓促地道?了声抱歉,就?快快离开了。
可?出了茶楼,只见沈徽音的夫君已经骑着马走远了。
她“啧”了一声,还是没想?起来人?家叫什么。或许跑得着急了些,这会儿心跳得好快,她按着心口喘了会儿气,想?着自?己去?胭脂铺子里找找沈徽音。
与此同时,歌楼的雅间内,曼妙的乐音飘荡着,袁彻一脸正气地杵在那里,显得十分格格不入。
年轻的乐伎掀开珠帘,打量两眼面前?之人?,端着笑容地走过?去?,朱唇轻启:“公子是要?听曲儿吗?”
曾青上前?一步,开门见山地问:“姑娘最近可?见过?吴妙锦?”
乐伎愣了一下,一脸迷茫,“你说谁?”
“姑娘不必装相?,我们既然能找上你,自?然是事先就?有?过?了解了。”袁彻淡声开口,给曾青递了一个眼色。
一张银票亮了出来。
乐伎眼眸微闪,笑了一声,又改了口:“公子莫怪,我的确是认识吴妙锦,不过?她之前?跟过?那大逆贼,你们突然问我,我不敢承认和她有?瓜葛。”
这便可?以好好问话了。袁彻说:“你们关系不错,是吗?”
“我们是同乡,之前?的确来往过?,不过?后来那个逆贼被惩处后,我就?没再见过?她了。”
“她没跟你说过?她去?哪里了吗?”
“我不知道?。兴许是逃命去?了,那个逆贼都被满门抄斩了,她是他身边的人?,不逃肯定会被牵连吧。”乐伎神色疑惑,“公子,那谋逆案不都是老黄历了吗,该查办的都查办完了,您怎么现在又来问这些呢?”
袁彻看她一眼,不动神色道?:“你也说吴妙锦是逆贼亲近之人?,我来追查她,自?然是上面的指示,要?将她这样的余孽缉拿归案。”
他瞧见乐伎的脸色几番变化,语气严肃地交代:“今日之事,不可?外传,否则……”
乐伎连忙摆手,“不说,我肯定不说。”
袁彻对她颔首,“多谢你的配合。”他让曾青将银票给她,转身离开。
出了歌楼后,袁彻对曾青吩咐:“派人?盯着此人?,看她会不会去?找吴妙锦。”
曾青点头应下,神情却突然一僵,“公子,公子……”
袁彻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正对上黎又蘅的目光。
适才黎又蘅在茶楼附近找胭脂铺子,走了半条街,都没找见沈徽音,没想?到会在这儿遇上袁彻。
她神色木然地看袁彻走到自?己面前?,扫了眼那歌楼,不咸不淡地说:“原来你也会来歌楼寻欢作乐啊。”
袁彻怕她误会,忙解释:“我今日是来办一些事情,不是寻欢作乐,之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的。”
冷风一阵阵地递过?来,糊到脸上,黎又蘅的脑子一阵冷一阵热,盯着袁彻感?到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