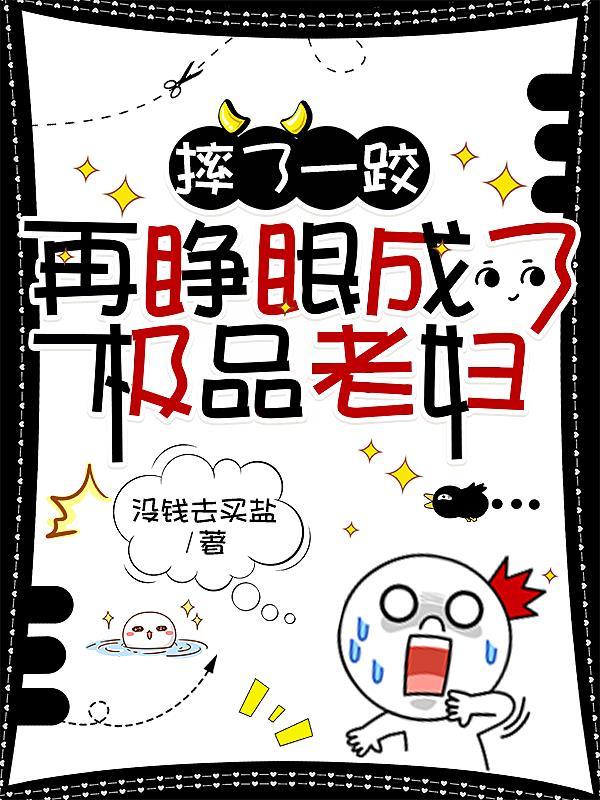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您哪位?_路沈半著 > 第32节(第2页)
第32节(第2页)
十三跟着点了点头,从怀里掏出半块玉玦递给花竹,说道:“这块玉玦,是当初你父亲给我的,如今物归原主。”
他说完,就出门去了,只留下花竹和方池两人在屋内。
花竹拿了玉玦,见这玉玦是阳刻的,不禁好奇,世间是否还应该有阴刻的半块。他单手摩挲着玉玦,有些心不在焉地往窗外看去:十三正坐在刘易的坟边,单手抚摸着墓碑,似乎在说些什么。
花竹忽然间有些想念父亲。
说起来,父亲去世这么久,自己都没有去坟上看过他。之前是因为他知道常家众人厌恶父亲,便从不敢去。后来花竹中了进士,想着定是要去一趟跟父亲说说,却因为接踵而至的事情耽搁了。
他暗叹一口气,又瞧了瞧窗外被用心打理的坟墓,心道不知父亲的坟上,现如今怎么样了。
但转念一想,自己父亲坟里埋着的,多半不是他本人。父亲真正的尸身,到底葬身何处,反而是无处可寻了。
花竹心下顿时升起一阵惆怅。
“青莲这人,你知道多少?”方池往花竹身边坐了坐,问道。
方池的问话打散了花竹心中小小的悲戚,他打起精神答道:“他是严管家的侄女,大概也是严丽君的堂亲吧。她本在常府外院伺候,但是去年我考中之后,外婆将她调到院子里面来了。”
他话中只称呼常府,并不说“我家”。
方池若有所思地看了花竹一眼,随后丝毫不掩饰地问道:“她是你的通房丫头吗?”
花竹脸一下子红了起来,方池看他那样子,便已经得到了答案。又问道:“那……你们有没有……”
“没有!”
“哦?为何?”
花竹脸上的红晕蔓延到耳后,“没有为何,这不重要,能不能问些跟案子相关的。”
方池见他如此模样,只觉可爱,言辞间并不退缩:“这就是案子相关的,她既然要接陷害你,总要有个理由。你们一直没有……咳……可能就是原因。”
“不是的,我跟她说过,若她有了心仪之人,我给她出嫁妆,送她出府。”
“若她心仪之人是你呢?”
“这怎么可能?”
“为何不可能?”
“就是不可能!”
一通争辩下来,花竹又羞又恼,只盼望着方池赶紧放过自己,不要再继续这个话题。无奈方池并不放过他,仍旧追问着为什么不可能。
花竹几乎快要急哭了,他不想说出这个事实,但对面这人又不肯罢休。他心下无奈,最终深吸一口气,毫无感情地、几乎一字一顿地道:“因为不会有人喜欢我。”
花竹说完这句话,起身想要逃离这里,他觉得自己不会被爱的事实,充斥着整个房间,让他无法面对。
方池却比他更快。
他一下子站到花竹的对面,双手用力扶着他的肩膀,让他无处可逃。
花竹几乎有些恨他了。
而恨又给了他一些勇气,让他可以怒气冲冲地盯着方池,他想着至少、至少让对方知道自己是在生气,而生气,或许比丢脸要稍好一些。
然后他听到不知道哪里传来的声音说道:“有的。”
那个声音如此温柔,如此悲伤,让花竹眼中升起的雾气最终还是变成泪滴落下来。然后他感到自己似乎进入了一个怀抱,那个声音变得近了一些,仍然一下一下地重复着“有的”,一下一下地抚慰着他的心。
他隐约知道是方池抱着他,又隐约知道这样不好。但是这怀抱太温暖,耳边的声音太温柔,让他只想一直这样下去。忽如其来的疲倦席卷了花竹整个人,让他此时除了掉眼泪,无法再做任何事情。
不知过了多久,方池松开了他。花竹不敢看向对方,低着头,一言不发地出了门。
第37章时疫难治,众目睽睽湿身
第二天,两人都没有再提昨日之事。方池只是问花竹是否睡得好。
花竹黑着眼眶,说自己睡得不错。
十三在刘易坟前烧纸钱,方池也掏出一叠,找了个背风的角落烧了,然后三人才上路。
出乎意料的是,三人返程临安,一路平安,连拦路的山匪都没遇到。十三不甘心,几次故意暴露行踪,赵青也都没有出现。一行人赶在花竹回城述职的最后一天,顺顺利利到了临安城下。
没想到临安城门却是紧闭,偌大的城门下或坐或躺,聚集着一群群的人。三人一打听,才知道现在往来通行要靠州府的文牒才能进城。
花竹和方池凭职方牌进了城,十三则径直折返,回泗州去了。
“我先回去和晓夏碰个面,看看有什么消息,我们晚些岳庙见。”方池着急回家见方晓夏,她只给方池传了一封速归的信,方池回信后,便没了消息,方池想着大概事情有解,也没有着急回来。
花竹点点头,往钱塘县衙走去。
临安似乎是下了很长时间的雨,今天虽然放晴,但一路上都是泥巴。等花竹到了县衙门口,一双靴子上扒着许多的泥,脚步都变得沉重了许多。
沈安澜领着一众官吏在后厅议事,见他回来,也不问捍海塘的进度,只是微微抬起手。他手掌向外,五指微张,却又无力握紧,最终改为招手,示意花竹一同过来商议。
花竹走近,就听到焦祁抢先说道:“花大人来得真及时,我们正推举你去治疫呢!”
花竹听他开口,便知道没有好事情。焦祁是秦合的表兄,秦合便是花竹出狱后,自杀的那个衙役。
“是出了什么事情吗?”花竹不理会焦祁,朝沈安澜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