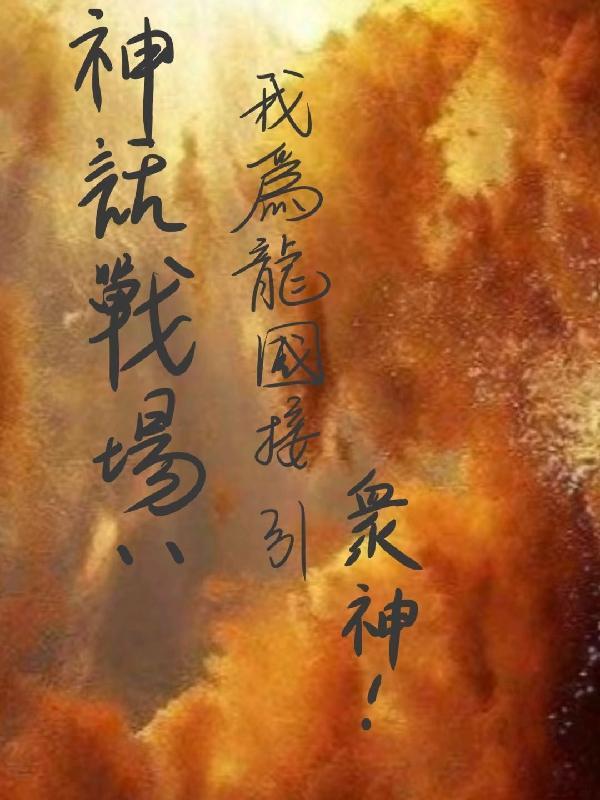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草原首领的京华明珠贵女txt > 第80章(第1页)
第80章(第1页)
卫修怪笑道:“那是。是我那天瞎了眼,看个女子在雨里一动不能动,生了点该死的怜悯。早知道是你赵越,我定不会!我定当场斩你头颅……”
昔咏亦冷笑:“哈,若是能早知道你身份,在见到你第一面,我就一剑刺死你了。也好过两年后,为我三千弟兄收尸——谁能想到崖下那位衣冠楚楚的公子,是艳压群芳的储君殿下呢?”
宣榕第一次见识到,昔大人也是有一张阴阳怪气的嘴的。
卫修被气得直喘粗气:“那你现在杀了我!杀了我啊!!!”
昔咏却很冷静地道:“不行。陛下说,在左贤王来齐前,你得好好的。所以,让我来劝劝你,殿下,别倔了,该喝药喝药,该上药上药。债得慢慢还啊。若非郡主当机立断,望都得死伤惨重,你万死不足。”
卫修哈了口气:“所以,你现在只关心我死不死,够不够给你齐国讹一笔,是吗?”
昔咏道:“这倒不是。我还关心细作有哪些人,你怎么和外部传信的。但这些你又不肯交代
,死士也都服毒没了,监律司的那些刑罚更不可能给你上,确实很让人头疼啊,皇太女殿下。”
卫修被气得说不出话了,过了很久,冷声道:“滚!”
“好的,告辞。”昔咏从善如流滚了,忽然,身后一道很沉闷的声音追问:“你当时……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吗?”
昔咏只冷冷道:“想多了。那天,我未婚夫来看我,所以我换了女装,去崖下,也只是为了给他寻一味治腿的药。您乔装打扮来我齐勘察地形,走夜路碰到鬼了罢了。”
长殿终归寂静。隆冬的光照孱弱,摇曳的树影稀薄。
不知过了多久,卫修沙哑着声音道:“来人……给我药。”
而头顶木板细微嘎吱一声,合上光影。
像是一曲折子戏落幕。
宣榕喃喃道:“怪不得……昔大人在邵关失踪过半月,原来跌落悬崖了……?被卫修……凑巧给救了?”
耶律尧则转了转手腕,凭借记忆,从她手里拿过火匣,意味不明地道:“真精彩。怪不得你舅舅让昔咏来劝卫修喝药,挺管用的。走吧,从这里回镇威阁,得一炷香时辰,我估计机关已经开了,容松又得跳脚了。”
火光亮起,宣榕还没从震惊里回过神来。
眉间的红痣愈发明艳,琉璃眸却像是渡了层水汽,她自言自语道:“这么多年,卫修估计是和天机部的人暗通曲款了。怪不得庭芝他们在北宫里查不出线索。”
耶律尧不置可否:“天机部是谢旻的地盘,想要自查,也得伤筋动骨一轮。他得头疼死。”
宣榕没再做声,直到走回镇威阁,快到甬道出口时,碰上了迎面狂奔的容松。
在容松忙不迭地告罪里,她整个人还是有几分迷茫的感觉。
这种感觉太过奇异,好像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暗流涌动。
然后寂寂无闻。
若非有人翻出,可能一辈子都深埋地底、不见天日。化为灰烬。
这种感觉让宣榕甚至有些魂不守舍。
走出甬道,头顶镇威阁机关大开,刺眼的白光让她眯了眯眼。
而宣榕出事,太子殿下显然被惊动了。谢旻焦急不安地等待良久,见她终于从甬道走出,还没松口气,又一副见鬼的样子瞪着她身后跟着的,悠闲自在的耶律尧。
再见宣榕一副眼眶微红、失魂落魄地样子,瞬间炸了:“他、他他怎么也在??!”
谢旻怒目而视,直指一脸无辜的耶律尧:“怎么哪儿都有你?你做什么了?”
除夕
耶律尧将火匣一关,在修长的指间转得令人眼花缭乱,他气定神闲道:“陪郡主四处逛逛。怎么,太子殿下吃炮仗了?火气这么旺。”
谢旻面沉如水,越过噤若寒蝉的随侍,在他面前立住,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今明两日,是使臣入宫的日子。你不该在此。”
“我又不是使臣。”耶律尧懒得和他解释,“去哪还要给太子殿下上奏请示不成?”
谢旻怒极反笑:“那你想以何身份出现在大齐?!”
耶律尧还真思索起来:“我想想。”
谢旻:“…………”
“……阿旻。”眼见又要掐起来,宣榕抬手在谢旻面前晃了下,打破针锋相对,以为他在怀疑是耶律踩了机关、挖了洞穴,才怒容尤甚,便解释道,“‘入瓮阵’开启,是方才为我取物,机关没合拢所致,和耶律无关。至于这个穴道……”
她不动声色前倾,用只有她和谢旻能听到的声音,道:“通往北宫。你要肃清天机部了。”
谢旻瞳孔微缩,很优雅地理了理袖摆,与宣榕交换了个意会的眼神。
他胸前四爪金蟒刺绣精致,翻出水波一般明灭的光影,金尊玉贵极了,但背对臣子侍从,脸色却也难看极了——不是方才迸溅出的怒意,而是阴沉冰冷的不快。
微抬了声,笑眯眯道:“哦?那正常,毕竟黑灯瞎火的,哪能走多远?还好表姐你及时回走,否则指不定受伤。袁卿,这事儿你来查,正月初三前,孤要看到结果。”
说着,谢旻转过身来,对着一名鬓发斑白的中年臣子道:“临近年关,辛苦你了。”
这位尚书,带着天机部特产——老实憨厚,诚恳地躬身接旨:“臣遵旨。为殿下解忧是分内之事,谈何辛苦。”
阿旻这是怀疑袁大人了,在试探。
宣榕暗自叹了口气,她自信谢旻能处理好此事,不打算插手,又想起未竟之事,对耶律尧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