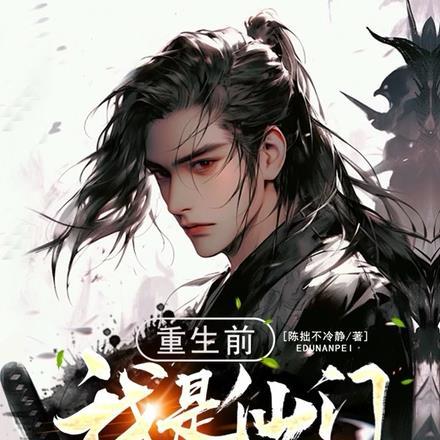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俏郎君mv内容 > 第27章 至少生仨大胖儿子(第1页)
第27章 至少生仨大胖儿子(第1页)
无意间被沈濯的话勾起心绪,安宁在转瞬间已经想了很多事情。
她回过神来时,见沈濯沉默着将白米饭一粒一粒往嘴里挑,明显神思不属的样子。
她用公筷给他碗里夹了一块肉,问他:“想什么呢?筷子都要戳到鼻孔里了。”
“没什么,就是有点想家。”沈濯怕安宁看出端倪,故意这么一说,也是他不想说话,只想堵住她的嘴而已。
因为他总不能告诉她,他其实心绪有些复杂。朝堂之事,他虽然有诸多不满,但他多年来随父驻守边疆,无力改变什么。
他出生世家,从小到大没怎么吃过苦,但是他在行军途中看到过很多穷苦百姓,他们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不惜卖儿卖女,只为一口饭吃,他们在拼命地想要活下去。
那时他路过时,因为见得多了,心里多少有些漠然。他认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们变成那样,或是因为懒惰、或是因为时运不济、或是天生命该如此。
他的内心甚至没有多少波动,更别说去将多少罪过推给朝廷、推给现行的制度,甚至推给他崇拜信任的君主。
很少,或者可以说,他几乎没往这方面想过。
可是这桃源镇,连一个正经的府衙都没有,这里的百姓却过得如此好,屋舍俨然、牛羊肥美,说起来,多少觉得可笑。
安宁不知他的心事,还以为他真在想家,一副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的模样,赶紧闭了嘴。
嘴贱!她就不该多嘴问!反而让自己被他将了一军。
因为手指受伤包扎得挺严实,她又连着掉了好几块菜在桌子上,神情看起来慌乱中透着点烦躁。
沈濯看不下去了,干脆拿起公筷替她夹了些菜放进碗里。
安宁犹豫了一下,索性放下了筷子,轻声问:“还没问过你家里的情况呢,你家里有几口人?父母安康否?”
毕竟,逃避不是办法,最有效的解决方法,还是直面困难。
她要是想和他好,这些问题迟早都要弄清楚的。
沈濯的筷子一顿,看着她的目光带上了几分戏谑,仿佛在说:我以为你只会用强,原来还会关心别人呢?
安宁被他看得心虚,但是她是什么人呐,她是土匪!
自我认知十分清晰的安宁面上十分镇定地迎视他的目光,她轻咳一声:“若是以后我们有了孩子,也可以接公公婆婆过来小住。”
沈濯被她的说辞给气乐了,他搁下筷子,沉声道:“不必了。我爹做点小生意糊口,常年不在家,我娘身子骨不太好,家中只有一老仆相伴,而我并无兄弟姐妹,乃家中独子。我们一家子福薄,可承受不来寨主给的这泼天的荣宠。”
又来了又来了,咋说着说着又生气了?听他这阴阳怪气的!日月可鉴,她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啊!
安宁无辜地瞪眼看他,虽然心里有点小小的歉疚。
毕竟,人家可是家中独子呢!她可就霸占了人家的独子呢!
但是这歉疚也就持续了不到两秒,她又痞痞地勾了勾唇,用包裹严实的手拍了拍胸脯,大包大揽地道:“没关系,有我在,至少给你家生仨大胖儿子!帮你家开枝散叶!”
沈濯握紧搁在膝头的指节,深呼吸,再次深呼吸……
几天相处下来,他觉得要活得长久,还是要学会自己调节情绪。
虽然……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