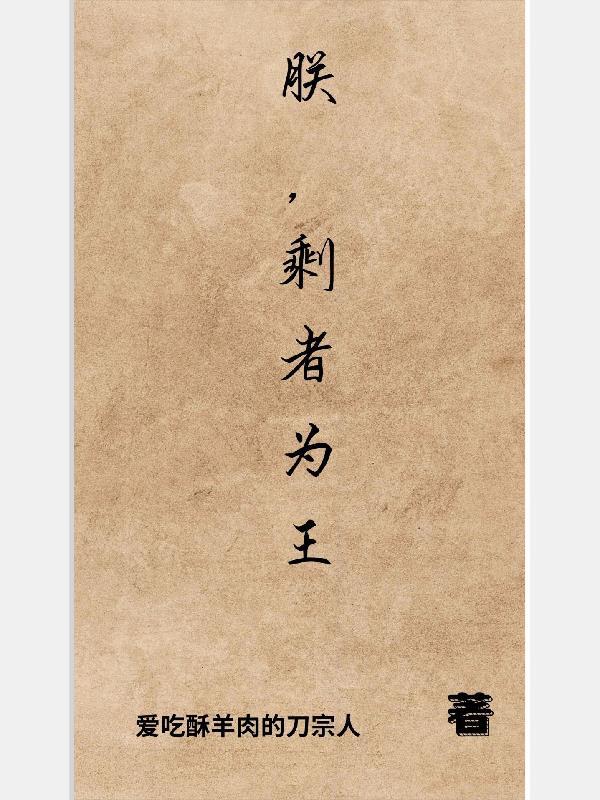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草木乡情 > 第56章 圣手隐于山村(第1页)
第56章 圣手隐于山村(第1页)
在偏僻的山区,村主任称得上是村老大、“山老虎”、土皇上,说话是一口唾沫一颗钉,他这是要为自家的媳妇儿找一个不花钱的“御医”呐。
“我……我实际上是被通缉的。”端木纳法咬了咬牙,透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我被抓了遗送回去算是命运多舛,可是不能因为你们‘隐藏通缉犯’而受到连累了啊!”
这村主任不傻,他了解到端木被通缉的来龙去脉后,便找个理由悄没声地去了一趟镇上,给派出所的所长送了些野味,喝了一场小酒,便打探得一清二楚,回村里悄悄告诉端木纳法:“你那边的通缉令是省内的,手续上其实不算合法,连网上都找不到。我问过了,只要不是全国的通缉令,在咱们这儿不管用。再说啦,全国的通缉令要通过公安部布,你们县里那帮贼心家伙有那个胆么?真要敢动那个贼心往上申请,上面审查起来,弄不好把他们巧取豪夺的行径暴露出来,反而自己先折进去。你就放一百个心,呆在村里吧。”
“我连身份证也没有哇。”端木纳法还是顾虑重重。“万一碰到查户口的,不就露馅儿了吗?”
村主任听到这话哈哈大笑起来。“你要身份证干啥?出门买火车票、汽车票?还是住旅馆啥的?咱这穷乡僻壤的,连个生人影子都见不到,谁来查户口?再说啦,镇上的派出所长是咱哥们儿,你又怕个啥。”
山里人性子野,常人难去的偏僻山村可以说是“法外之地”,天高皇帝远地没有多少人认真去查去管。端木纳法可不敢拂了村主任的“好意”,就这样被强留在金大夫老家这个山村里。村主任算是土霸王,他瞒住上面不吭气儿,村里人谁乐意没事找事?更何况人家有一身好医术,在这缺医少药的地方,他们巴不得让这尊“神医”留在这儿呢。
让端木纳法惦挂的,是他从承德那座县城逃出来的时候,除了些许现金和随手取走的一些珍贵中成药之外,主要还是祖传医书药籍和多年来搜罗到的从宫廷到民间的秘方。潜逃和流浪的时候,他一直把这些东西装在一个挎包里随身携带着,寸步不离身边。那天从悬崖上摔下来之后,挎包落在深山里,这是他的命根子呐,必须要找回来!
金大夫说到这儿,几个声音齐刷刷地响起来:“找到了吧?”
金大夫又是摇摇头,满脸落寞,令众人瞠然。
被强留在山村后,端木纳法借着为村主任的媳妇疗伤保胎采药为名,多次再入深山,在那悬崖下及周边寻觅丢失的挎包。深山里长年雾锁烟迷,湿瘴极重,山里的野物又多,再加上他跌落崖下是在一个多月前的事,挎包饱受风霜雨露和动物扒拉,找到后也让他大失所望:挎包里除了那点珍贵的中成药有较坚实的包装盒而得以幸存外,医书药籍和抄本笔记连同不多的钞票全已霉烂,能找到的残页要么支离破碎,要么字迹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了。
“真是太可惜了啊!”房间里又是几声沉重的叹息。
“看样子,我们只能在支医为老乡看病的同时,走乡串村通过端木大夫给治过病的老乡那里摸点儿线索喽。”龚国安深深地吐出一口闷气,不无遗憾地叹息道。
房间里众人点头称是。
“端木大夫的那些秘方必定对医学界、尤其对我们的科研攻关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价值。哪怕是残片或口传都不可忽视!这项既定任务总要想办法做好呐。”龚国安下了结论。
“谁来做呢?”中医科老主任问道。他的话一出口,房间里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同一个人。
金大夫的嘴巴嗫嚅了一下刚要开囗,佟欣副院长推门进来,大嗓门地嚷嚷道:“龚院、禹老师,诸位,出来吃饭了。”
按照镇上的安排,本来是要在镇里一家叫“野山居”的小酒楼里摆几桌的。怎奈一来文副市长和县长剪彩揭牌后早早地走了,二来四方八村的老乡们蜂涌到卫生院,排着长队候着市医院的名医们给看病,童院长他们忙的连口水都顾不上喝几口,又哪有空去酒楼端杯把盏呢。
这也难怪出现这般状况,须知丛山深处的乡镇原先的医疗条件那么差,缺医少药且不说,老乡们想去市里的大医院看病,往返四五个小时的车程就让大多数乡民却步。在原先那小小的乡镇卫生院,即便是找那几位半瓶子水的大夫看看,哪怕是只拿块把钱的感冒药啥的,挂号费都要缴两块钱。市医院这回来的大都是科主任一级的专家,至少也是副主任医师,专家挂号费几十百把块还一定能排得上队,眼下名医萃集义诊,虽说也要按规矩缴两块钱挂号费,这可是几十载难逢的机会呐,凑到跟前想查病诊治的老乡几乎挤破了脑袋。
义诊的大夫们忙的团团转脱不了身,负责后勤的佟欣副院长只好与镇上商量了一下,换成盒饭送到卫生院,让大家凑合着轮流吃点好填饱肚子。
龚国安几位走出来看到这情景,二话不说,快步走到童院长那间诊室前,挤开人群对童老说:“童院,我来替您一会儿,您先去吃几口垫垫去……”
中医院老主任和金大夫也照猫画虎,各自找了替换的对象接诊,让他们轮流去吃口饭。
禹若冰他们刚才听金大夫汇报的房间成了临时餐厅。乡里的酒楼条件委实简陋,连快餐盒也没有,佟欣副院长索性让人把酒楼做好的七八大盆菜肴全端进来,大伙儿端碗盛上饭,再随意勺上菜,吃上了“自助餐”。
童院长一边吃饭,一边听禹若冰转述寻觅端木大夫踪迹的进展情况,同样感概地说:“这端木端的是位了不得的人,不过他受此迫害颠沛流落到此地,也算是造化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