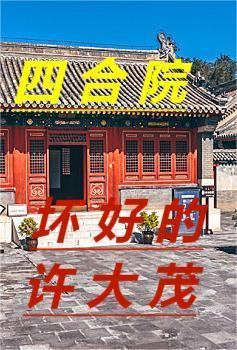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对抗路笔记 > 第79章(第2页)
第79章(第2页)
她推着小电车在漫天大雪的冬夜里,一步、一步、走回了学校。
次日,她看着对面诚恳道歉解释,甚至带来一堆保暖用具的秦屿。
对上秦屿满目心疼的眼神,她不甚在意轻轻笑了笑,告诉他不必自责,她没放在心上。
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本身就是一件很愚蠢的行为。
她是多么的善解人意,她想。
然而,秦屿又一次沉默下来,什么也没说,无声地给她带好围巾,帽子,手套,带上她去吃了顿火锅,在当天晚上,又回了江北。
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不高兴什么。
而第三次,也是他们分手的那一次。
她前往江宁去看秦屿的散打比赛,
擂台上摘掉金丝眼镜的秦屿,毫不掩饰地露出自己的野性,充满攻击性的眼神,蓬发的肌肉,死死锁定敌人的招式。
和他平日里清冷禁欲的模样大相径庭。
她看的有些发愣,总感觉眉眼间,特别熟悉。
就是这一瞬的愣神,秦屿比赛结束,台下的学妹欢快像他表达了祝贺,并递给他一瓶水。
他没接,定定看向她。
而她回过神来,大方地摆摆手,示意自己不介意。
就在比赛结束的晚上,在江北大雪纷飞的冬夜。
万籁俱静的街道,路边昏黄的路灯散发着朦胧的光,
他们站在路灯下,彼此沉默看进对方的眸眼。
秦屿一动不动,任由雪花肆意落在他鸦羽似的头发、肩上,却固执地给她打上一把伞。
他鼻梁仍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依旧是他那双没什么波澜的眼睛,一如既往,沉默寡言。
直到——有一两片雪花落在他半垂的睫毛上,摇摇欲坠。
他方才伸出手,将绕在脖颈上的围巾取下,拢在她身上。
而后,
还是那副平静的口吻:
“季知春,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
他一向聪明的,她早该知道。
或许他早就看破她那点上不得台面的心思,只是一直没说。
小心思被戳破,她也没有丝毫的惊慌,反倒是心里那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而同时,一丝愧疚萦绕在她心头。
她说:“对不起”
秦屿还是一贯淡漠的表情:
“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
秦屿的底色还是温柔,她想。
时至今日,季知春看向眼前的秦屿,虽然神色未动分毫,一贯的淡漠冷静。
但,那股愧疚又一次缠绕在她心头。
“对不起,秦屿。”
“当年,是我不懂事。”
“你没有对不起我。”秦屿淡淡开口,他看向眼前那个愧疚都要写在脸上的女孩,又恢复到一贯冷淡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