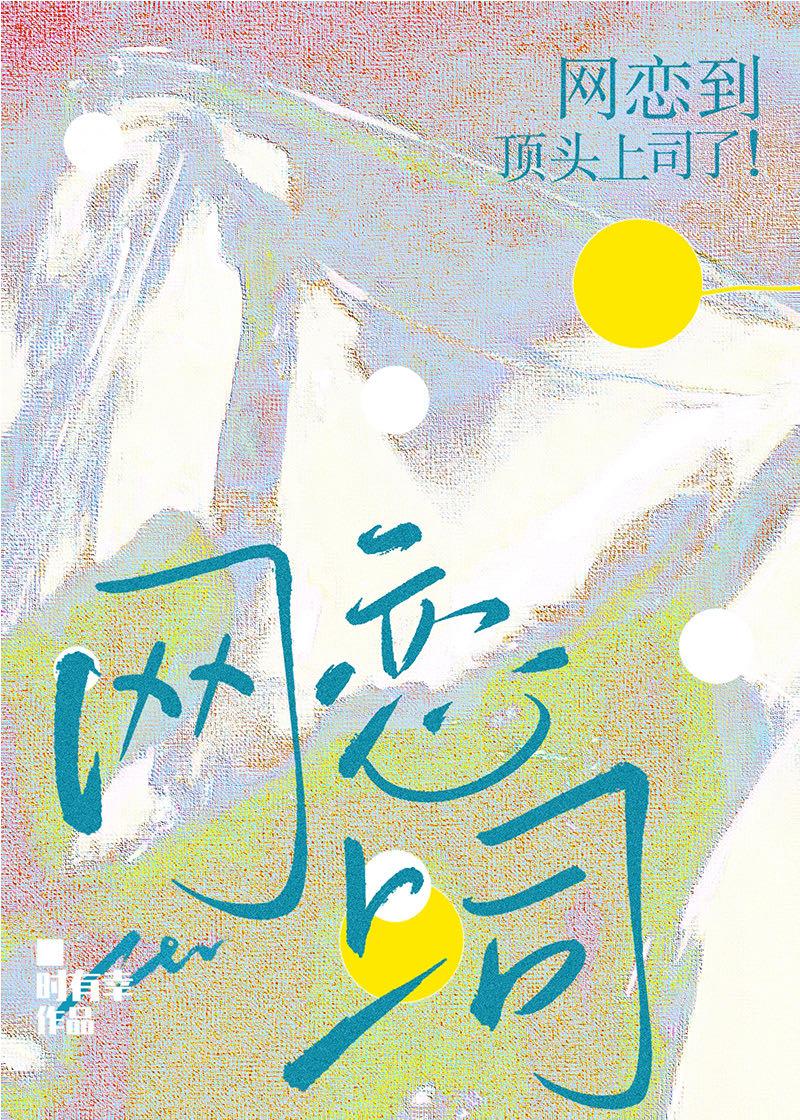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红楼之林如海的妾 > 第11頁(第2页)
第11頁(第2页)
林如海滿腦子這麼想著。
黃大學士名聲在外,講課卻十分枯燥,也不知為何還能教出這麼多名家,大約是他們走馬觀花,沒有領會到妙處?
散了學,蘇哲關心問他:「你可是尚未痊癒?」
林如海這幾日又吃又玩,精神百倍,哪裡有病的樣子。他都這麼有活力了,落在蘇哲眼中難不成還是病懨懨的?
林如海拱手:「蘇兄多慮,只是忽而犯困。」
蘇哲和他一路走著,邊抱怨道:「方才那題好刁鑽,好端端的問什麼政事,海貿和兵戈,豈是我們能隨便議論?」
又不是殿試,出這樣的題目確實綱。
不過林如海腦袋空空,他方才隨性迷迷瞪瞪寫的東西,但願能矇混過去。
兩人正走著,林如海被人用扇柄敲了一下腦袋。
回頭一看,原是蘇學士。
這幾日林如海閒適得過分,對著常安沒壓力,現在看到蘇學士,忽而有些心虛。
蘇學士沒看到文章,他們寫的東西當時就被收走了,但是蘇學士老遠看見林如海的答卷上有一大團墨漬。
老學究吹鬍子瞪眼:「如海,回去好好練字,這般文墨呈遞上去,縱使你文采飛揚,不取!」
林如海還能如何,縱使他前世活了四十來歲,在蘇學士跟前仍舊是晚輩,只得垂認錯:「是,學生知錯了。」
今日作文的學子不曾知曉,他們的文章雖是鹿白書院的黃學士收走,當夜就有幾篇輾轉呈遞到禮部尚書黃大人手中。
蘇學士和黃學士老友相見,當然要多聚幾回,至於從江南帶來的學生,也跟著沾光。
如錢牧和陳香這等將近天命之年,對下一回會試給予厚望者,自是與有榮焉。
而蘇哲卻是十分厭煩,卻又不得不來。至於林如海,談不上厭煩,只覺得疲憊。
幾人入席落座,林如海這等小輩坐在次席湊。
忽而黃學士引著一藏青提花綢衫的男子進來,當下有人認出來人就是尚書黃大人,趕緊起身行禮。
黃大人面上笑容溫和,抬手讓眾人落座:「只是家宴,湊巧而已。」
黃大人入席,眾人才姍姍落座。
尋常家宴?
林如海可沒年輕時候那麼單純,也不知尚書大人葫蘆里賣的什麼藥,明年才是會試之時,席面上的舉子,能在會試題名者寥寥,這位大人籠絡人心的戰線拉的可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