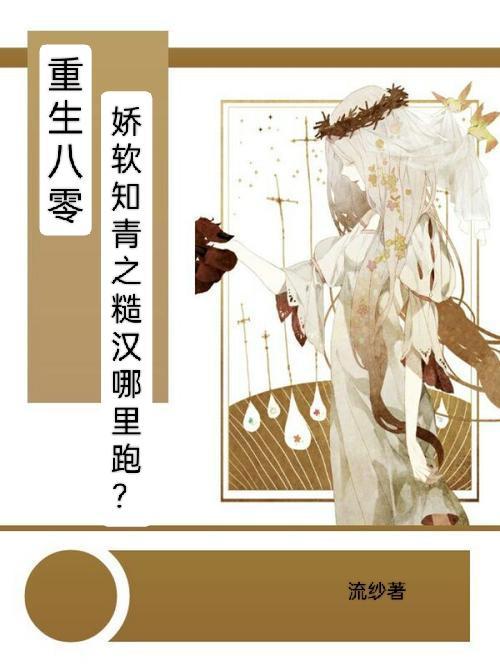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公主为上长佩 > 第67章(第2页)
第67章(第2页)
盏中茶汤上飘了一片枯叶,萧敛意轻挑去了,两指一松,便被卷进了寒风中。
徐忘云独坐在长廊上,头顶黄铜铃铛随风轻声作响。他神色平静,正望着青灰石瓦廊下透出的一方天色出神,脸侧却忽地一热,是被萧敛意捧着一盏茶贴在了他的脸颊上。
“阿云在瞧什么?唤你半天也不应我。”
萧敛意在他身侧席地坐下,徐忘云接过茶盏,垂下眼轻轻摇了摇头,并未答他。萧敛意仔细端详他侧脸半响,自然知道他心下所想,却也只能佯装不知,起了个无关的话头,“阿云尝尝,这是宫人新采买来的戴胜香,据说城外一叶千金十分难得,你快尝尝看,是不是真有他们说得这样好?”
徐忘云依言尝了一口,简短道:“好。”
这句点评给得敷衍,萧敛意却也罕见地没多纠缠。他将自己手中的那杯放在一旁,抱着双膝歪着脑袋瞧他,瞧他面色平淡地望着别处,哪怕席地而坐脊背却也挺得笔直,不由轻笑了声,忽伸手撩去了他额边被风吹乱的头。
他这样隔三岔五的动手动脚徐忘云早已习惯,只看了他一眼便再没给什么生动的反应。萧敛意手指牵着他那缕丝滑到他的耳侧,指尖轻轻地蹭过他的眉尾,却也不敢再有什么别的动作,缓缓收回了手,落回徐忘云看不见的地方,又将那根指头悄无声息地攥进了掌心里。
这一套鬼鬼祟祟又满怀少女春情的动作徐忘云自然丝毫未察,两人各都静下来,一红一白两个影子,便这样默不作声地坐了许久。廊下系着的黄铜铃时缓时急地摇晃着,天地一隅,便只剩这只铜铃轻响,和远方隐隐传来的鸟啼声。
桃蹊揣着一封书信匆匆入了院,一脚踏进大门见着此景面色当即一变,正欲转身就走,萧敛意却在这时叫道:“桃蹊。”
桃蹊如临大敌地转了身,萧敛意冲她招了招手,示意她将信拿来。桃蹊于是小心翼翼地递给他,萧敛意展开看下去,见那上面只有言简意赅的两个字:明日。
徐忘云问:“谁的?”
“棠儿的。”萧敛意将那信随手折起,丢回了桃蹊手上,“说在外仍寻不到陈簪青的踪影,问我还要不要继续找下去。”
徐忘云不疑有他,“陈医师还未寻到?”
“谁晓得她是跑到哪里去了。”萧敛意对桃蹊道:“去给棠儿回封信,写知道了,自去就好。”
桃蹊应了声,忙捧着信纸匆匆跑走了。徐忘云关切道:“陈医师不在,你的药还有多少?”
萧敛意笑道:“阿云这是关心我?”
徐忘云道:“你只回有多少就好了。”
“不慌不慌,还剩许多呢。”萧敛意捧着脸瞧他,“她临行前给我留得这些,足够我吃上许多时日了。”
徐忘云嗯了一声,又扭回了脸。两人各自的茶盏皆被仍在身旁,这城外一叶千金的茶汤早已暴殄天物地凉了个透彻。萧敛意看他许久,没话找话道:“阿云近来睡得好不好?”
徐忘云瞧他一眼,短促回道:“好。”
“可有做梦?可梦见什么了不曾?”
徐忘云说:“不曾。”
萧敛意有心想与他多说几句话,又道:“那阿云……床铺软不软?要不要我传人给你换一床新的来?”
徐忘云侧头看他一眼,不再回话了。
“我近来总觉得床铺睡得不如从前软,枕头也不似从前般舒服,你说是不是这个我才总做梦?前些日子我听宫人说京城里有个姓梁的纺织娘很会做被褥,你说,我若传人去买一床来,是不是便能睡得更安稳些……诶!阿云!你去哪?”
他絮絮叨叨讲个没完没了,徐忘云实在听不下去,起了身往屋子里走了。萧敛意见他要离开,旋即不乐意地叫了起来,徐忘云路过他身侧时,便顺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权当做安慰。
这安慰好似一阵轻风,转瞬即逝地拂过他的肩头便散得无影无踪。但他的手离开时,却又有个什么东西顺着他的肩头掉进了他怀里。萧敛意狐疑地捡起来一看,见那从徐忘云手心掉进自己怀里的,竟是一块包的仔仔细细、个头小巧的饴糖。
“……”
他捧着这块小小的饴糖,半响说不出话,好半天才哭笑不得地说了句:“阿云拿我当孩子哄?”
徐忘云的身影早就进了门中,连一片衣角也再看不见了。
宽阔的长廊上,萧敛意独坐在上面,捧着那块饴糖,半响再没了动静。
廊下的黄铜铃铛“叮当”一声轻响,便又重归了一片寂静。
次日,冬月甘九。萧载琮如约乘车到了兰渡寺,身旁,还跟着身披凤袍的皇后。
皇后神态平淡,头顶珠冠在日晖映照下闪着华美光芒。萧载琮携她拜完了神佛,当晚照例留宿一宿。到了夜里,萧载琮与皇后回寝房的路上,却撞上了个身形匆忙的灰衣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