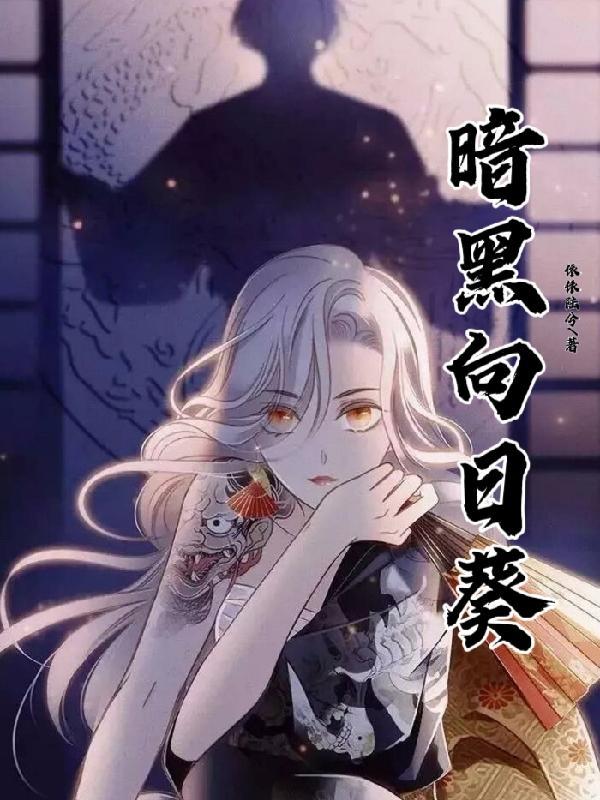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每次都拐进恋爱线的红黑游戏 时渐鹿 > 23 晋江独发二合一 死者可以为大但(第3页)
23 晋江独发二合一 死者可以为大但(第3页)
见琴酒目光不善地盯着两人的背影,他愣了一下,“……大哥?”
琴酒垂下眼,控制着自己的视线看向指尖的烟蒂,“嗯。”
“我是说,我听警察的对话说,那个少年侦探就是那个工藤新一,我们这事不妙啊。”
琴酒将手中还没抽完的烟蒂直接按灭在墙上,“不会。”
普通人经手的案子破绽太多——比如眼前这个。
但他们动手,一个年轻的小子还不至于找出破绽。
比起那少年“侦探”的头衔,或许连他自己都不会承认,他更在意的,是那个披着那少年外套的人。
她被他抱下过山车的样子琴酒还历历在目,说是“抱”其实并不准确,当时她已经脱力,连自己倚靠的人都没有知觉,只是无意识地靠着身边最近的人。
但他就这么自然地将手搭在了她的肩上,伸手拨开她被鲜血糊住的半捋留海,然后将自己尚带着体温的外套,裹住了那副躯体。
她被他们的朋友簇拥着坐到一旁,端水、擦脸、安慰、打闹、喂糖……而他只能在角落里远远看着,甚至控制着自己的目光,不至于过于明显,被那群嗅觉灵敏的侦探们发觉。
而她恢复知觉的第一件事,就是朝他们笑。
白着脸、抖着唇、攥紧身上的衣服,对着那人笑。
……他还是只能在角落里看着。
就像现在这样。
琴酒的目光收束得很好,忙着观察案情的津木真弓没有丝毫察觉,她完全被爱子背包中那柄染血的菜刀吸引去了注意。
“警部,从被害者的女友爱子女士的包中搜到了这个。”
目暮警官看着包里的菜刀,沉吟一会儿,“将爱子女士作为重要参考人,带回警局。”
津木真弓皱眉,刚想开口阻止,旁边的工藤新一比她更快。
“等一等!目暮警官,这位女士不是凶手。”
目暮警官也皱眉:“但是案发时间,只有她坐在死者身旁,背包里也搜出了菜刀……”
“菜刀不是凶器。”接话的是伊藤行人。
他伸手,将自己那身首异处的骨架递给目暮警官。
“爱子女士背包里搜出来的菜刀,和我手上这柄差不多大小和锋利程度,而我手上这柄,是用来砍这幅骨架的头颅的。”
他指着骨架上的切口断面道,“这样大小的菜刀,砍没有血肉和脂肪阻拦的微缩骨架,切口都没有那么整齐,更不可能在那么短时间内砍下比骨架大数十倍的真人头颅。”
说着他瞥了一眼旁边正哭泣的爱子女士:“除非这位女士是一位深藏不露的杀手。”
津木真弓:……深藏不露的杀手确实在场,但不是这位女士。
工藤新一点头,拿出了口袋中的一颗珍珠:“这是我在案发的山洞中找到的,可以指明凶手的决定性证据。”
爱子的另一位女性朋友捂嘴惊呼:“这、这好像是小瞳的……”
“没错,凶手就是坐在死者前排的这位精于体操的小瞳女士。”
说着,工藤新一解释了一波那令人叹为观止的体操手法,手法的极限程度让津木真弓都摇头咂舌。
……在疾驰的过山车上使用这么极限的手法,一不小心没头的就不是死者,而是凶手了,多大仇啊?
小瞳自然不认:“项、项链是坐过山车的时候不小心散架的,而、而且爱子包里的刀又怎么解释?你、你说是我,有什么证据?!”
津木真弓看了一眼爱子的背包,询问着旁边已经完全手足无措的爱子:“你上一次打开这背包是什么时候?”
“坐、坐过山车前,我、我们去了一趟卫生间……”
“如果我没猜错,当时你把背包交给了小瞳,让她帮你看着,从卫生间出来后,就直接背了上去,然后来过山车排队了?”
“对、对……”
津木真弓看向小瞳:“那么,我就是证据。”
目暮警官惊讶道:“津木君?”
“早晨入园的时候,我与伊藤同学不慎和两位女士发生了一些摩擦,当时有过一部分物体与肢体接触。”
津木真弓看向小瞳,毫不意外地看到了对方骤然惨白的脸色。
“想起来了,对吧?你应该是准备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背包,将这柄染血的菜刀塞在了里面,然后在爱子上卫生间的时候替换掉了——但换得了包,换不了包上的指纹。”
她上前一步,逼近小瞳,伸出自己的双手,手上套着办案专用的手套。
“如果现在我们拿这只包去检测,你觉得会得出什么结论?——为什么早上我们碰过的包,却在包上检测不出我们的指纹呢?”
眼见铁证如山,小瞳终于跪倒在地,开始了痛哭认罪的流程。
紧接着便是一段“她爱他他爱她他不爱她”的狗血戏码,津木真弓听得索然无味,撇了撇嘴,默默朝人群身后退去。
见案犯已经认罪,旁边的伊藤行人走向津木真弓,压低了声音。
“早上的时候,我没有碰到她的包。”
津木真弓侧目。
“你也没有,你只碰到了她的伞。”
津木真弓轻笑:“早上情况混乱,你撞了对方,而我又抢先伸手碰到了对方的东西,除非是像社长那样的超忆症,没有人可以肯定自己当时的记忆——只要她不敢肯定‘我们没碰到过’,她就已经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