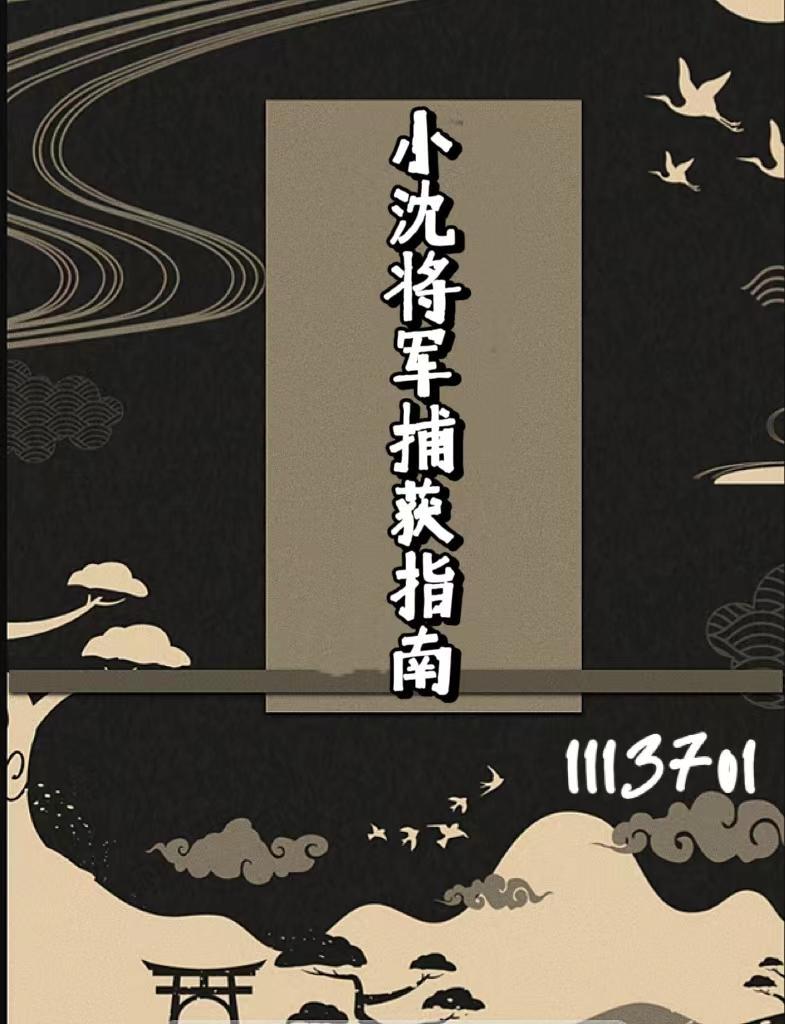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蜘蛛免费阅读 > 第7页(第1页)
第7页(第1页)
“你确定他不是电锯狂魔吗?他差点割断了你的颈大动脉!”艾德里安生气地把手中的马克笔丢到桌面上,“而你居然还邀请他上床!你以为你在演什么,‘沉默的羔羊’?”
“不,我相信是这是一部‘肖申克的救赎’,当我说到德里克的微笑时,他感动得都快哭了,我猜他从没像现在这样深爱着他可怜的表弟。再没有什么比向自我感觉优越者展示出对手的软弱更令他得意的了。”
“如果德里克还活着,他或许会在他身上少刺两刀。不过,我还是很难想象一个教父会说出那样的话。”
“当然,德里克压根就没说过,他从来就不是个感性的人。”杰森无所谓地耸耸肩,“当我对他的戒指表示好奇时,他很爽快地脱了下来,戴在我手上,然后说:‘宝贝儿,你看,它太宽了你戴不住——看来我的尺寸比你大。’‘尺寸’那个词他说得色情极了!”
艾德里安认真地看了他一会儿,说:“杰森,你不能老是这样,这太危险了。”
杰森微笑起来,“像在悬崖上攀岩是吗,而且不系安全带?这样才够刺激,而且我从来没有摔下来过。你不知道,当德里克的手下用枪顶住我的脑袋时,我确实有点后悔把红酒泼在衣领上,不过这念头还不到几秒种就消失了,比往热水中扔冰块还要快。我就是喜欢这种与危险擦肩而过的感觉——用我的魅力对抗它,然后我赢了!每一次!”
“至少这次你被割了半圈脖子。”艾德里安严肃地说,“也许下次是一整圈儿。”
“不会的。”
杰森双手枕在脑后,把一双笔直的长腿悠闲地架在沙发背上,t恤下摆滑落下来露出结实的腹肌,腰部的线条有力地收缩成完美的形状。“那家伙迷上我了,虽然他自己还不知道——不过没关系,他可以用下半辈子的时间,慢慢发掘自己身上潜藏的同性恋倾向。”
事实证明,文森特并不像杰森说的那样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半个多月后,他就出现在杰森的面前。
“你的伤怎么样了?”他问。
“哦,好得差不多了。我跟老板说这算是工伤,于是她放了我一天假——她是个仁慈的吸血鬼,不是吗?”
文森特笑了笑,他看上去显得有点不太自然,“我明天准备回意大利,所以今晚想来找你证实一件事。”
“什么?”
“我想知道,跟男人上床究竟有多么让人无法忍受。”
杰森愉快地笑起来:“我可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那和跟女人的感觉完全不同。”
于是,求证者与证明者一同滚到了酒店豪华套房的床上。
当杰森毫不做作地脱掉全身的衣服时,文森特发出了一声不由自主的赞叹:“真是……漂亮极了!像古希腊雕像,只是它们不具备这样的弹性和温度。”他抚摸着他身上的每一寸象牙色的紧密肌理,感觉包裹着匀称骨骼的肌肉是如何年轻而健康地收缩舒展,蓬勃着生命力与美的诱惑。或许男人的身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令人难以接受,他想,至少眼前的人是这样。
他开始亲吻杰森,像跟女孩儿约会一样,细细地舔着他的嘴唇,后者顺从地张开嘴放他的舌头进来,然后开始技术娴熟地反攻。像两只被情欲灼烧得饥渴的野兽,两个人纠缠在一起,用自己的皮肤用力摩擦对方的身体,在床上翻滚,扭动成各种姿势。
关键时刻文森特停了下来。他不太确定是不是要那样做——倒不是因为他不想,他已经硬得不行了,只是他怀疑那个地方真的可以容纳男人的性器吗,它的入口紧闭着,连塞进两根手指都有点困难,里面像吮吸的小嘴一样有力地收缩……
“如果你不想干我的话——”
杰森沙哑着嗓子说,翻身把他压在下面。文森特能清晰地看到他濡湿的金发粘在脸颊和脖子上,一根根细碎的金丝般纯粹,瞳孔因为欲望的催促而沉淀成了深深的墨绿,却像要在晦暗之中放出一道亮光,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旺盛地燃烧,那是属于黑夜野兽的放肆张扬。“其实我更喜欢在上面,要不让我干你?”
被挑衅的男人从喉咙口挤出一声咒骂,动作粗暴地把他从身上扯下来,毫不留情地从后面刺入了他的身体,开始用力抽动。
“你是个野蛮人吗?我快被你的匕首捅成两半了!”杰森喘着气抱怨道。
“那可真抱歉,或许我该给它戴顶礼帽,绅士风度地敲敲门,问可以进来吗——男人之间是这么做的?嗯?”正进出他身体的男人毫无诚意地说道,接着发出一声满足的喘息,“放心,你那儿的适应性强着呢,它正紧紧地夹着我……天,这感觉真棒,我应该早点尝试的……”他以胜利者的姿态享用着汹涌而来的欲潮,那是自身肉体官能的强烈愉悦与对另一具强健的同性肉体的彻底征服融合在一起的绝顶快感,他奋力地冲刺,疯狂地晃动,兴奋地叫喊道:“真他妈的太棒了!”
杰森用手臂撑着床垫,低头看自己股间软垂的性器——它被完全忽视了,或者是另一个男人下意识地不愿意去触碰它。但这没什么大不了,人总会想办法让自己得到满足不是吗,他在嘴角边翘起一丝嘲讽的微笑,空出一只手去套弄它,看着它逐渐勃起。
他自慰,最后达到高潮,同时让身上的男人尽兴到了极点。
他们在床上厮混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当杰森醒来的时候,文森特已经打扮得衣冠楚楚。他对床上睡眼惺忪的帅哥露出一个抱歉的笑容:“9点的飞机,恐怕你得一个人吃早餐了。”
“一路顺风。”杰森打了个呵欠,翻身抱住一只大枕头继续睡。
他那副满不在乎的腔调把文森特的脚步从门口拉了回来。后者大步走到床边,有点恼怒地责问:“你怎么能这么无所谓?”
杰森正要说什么,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不好意思,我得接个电话。”他懒洋洋地按下接听键:“喂,艾德……是啊,我还在睡觉……呃,抱歉,好像我昨晚出去的时候踢翻了一盆,我不是故意的,院子里光线太暗了……哦不不,我绝对没有仇视它们,尽管它们总像喝了促生剂似的疯长,像巫婆的头发一样相互缠绕,每次都把我的窗户堵个严严实实……”
文森特看着这个一边对着电话嘟囔,一边像是又要睡着的家伙,无奈地叹口气,“听着,我必须回去处理一些事务,家族首领的更替可不是件容易事……我会回来接你,乖乖等着,记住别给我另找情人!”
杰森朝他随意挥了挥手,或许根本就没听清。不过没关系,他无须跟他商量什么,也没必要征求他的意见。
直到文森特离开客房,杰森还在煲他的电话粥。
十五分钟之后,他听到了由远而来的警笛声。杰森跳下床,光着脚跑过去,从十四楼的窗户往下望,看见几辆亮着灯的警车和救护车停在酒店门口,一堆人在下面叫喊着跑来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