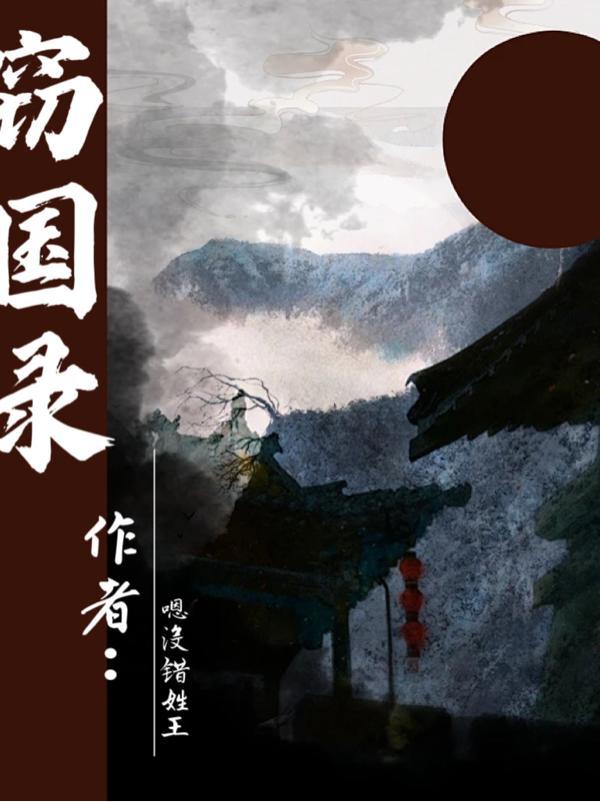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权臣上位手册女尊番外 > 第304章(第1页)
第304章(第1页)
一句话将慕容霄的自持击碎,他颓然一笑,“现在不算了。”
在房州时她曾许多次守在城门处等他,相送却是不多,因为那时她们都知道,慕容霄会很快回来。
荣蓁微微仰头,将眸中的泪逼退,她平复许久,道:“那年在襄阳,我去找过你。”
慕容霄却道:“我知道。”
即便无人告知,他也知道荣蓁一定去寻过他。
慕容霄的眼神落在不远处送别的行人身上,相拥而泣,依依不舍,而他与荣蓁之间隔着数步之遥。他的手紧了紧,行动间连他自己都惊住,五年之后,他再度抱紧了荣蓁,“若有来生,一定是我,对吗?”
荣蓁任他抱着,眼泪砸落在他肩上,“我这样的人,这一世伤人无数,哪里敢许人来生?”
慕容霄眼眶泛红,伸手拭去她面颊的泪,“荣蓁,我从没有后悔过与你相识,哪怕有缘无分。我也没有那么可怜,我有慕容家,有澜儿,无需因我自责。”
深秋透着凉意,怀里的这份温度很快便留不住,在温热尚存之时,慕容霄松开了她,“保重。”
慕容霄转身走向马车,掀开车帘时,他的手指微微颤抖,直到身影被帘幕挡住。
马蹄声重又响起,马车从她身旁经过,荣蓁扯过马的缰绳,慢慢向城内而去。
—
再回郑府时毒医已经离开,经过这几日诊治,郑玉的面色比从前好了许多,气力也恢复不少,她让侍人都退下,留荣蓁单独说话。
郑玉目光柔和,轻声道:“先前总想找机会同你说说话,可我没什么力气。阿蓁,我的身子我自己有数,你不用为我而自责。”
今日已经两个人告诉她无需自责,荣蓁握住她的手,愧声道:“若非我的嘱咐,你又怎么会那样放心明苓,又怎么会毫无防备。”
郑玉摇了摇头,“那也不是你的错。我是朝廷官员,去蜀中本就是奉命行事。”
荣蓁的眼神由愧疚转为怨恨,“我不甘心,凭什么,凭什么她们皇族之人为了自己的私欲,野心,这样置臣子的性命于不顾。若非吴王的野心太盛,当年你不会在江南平叛。若非明贤忌惮她的长姐,你也不会像今日这样连说话都没了力气。这中间有多少人的性命白白丢弃,天下人都不过是她们的棋子,她们高高在上,以她人人命做筏,来巩固权位。你当年问我为何不肯回京,偏要守在襄阳那地方待上数年。因为我怕了君心难测,厌恶朝堂上尔虞我诈,我想寻一个地方好好生活,用我手中的权力替百姓做些事。可她们呢,她们又做了什么?”
难道就因为郑玉没有死,她就可以不怨恨明贤韩云锦之流?她还没有这样伟大。郑玉是活着,连离开床榻都难以支撑的活着,没有几年时光,一点点耗尽的活着,让她怎能不恨!
她的手指被郑玉握住,“阿蓁,你年少时说自己不愿做官,如今却做了摄政王,命运本就难测。我不在乎韩云锦那些人,我只是不想t看见你不快活。我不在府里的这些日子,一直都是你在照料,我们本就不是寻常朋友,是生死之交,莫逆于心,你若是总沉溺在这些恨意里,我会心疼。”
荣蓁伏在郑玉手边,默默留下泪来,“阿玉,我们该怎么办?”
在朝堂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摄政王,如今无助的像一个孩童,郑玉摸着她的长发,只道:“随遇而安。”
—
内室昏暗,姬恒却依旧看得出荣蓁的异样,他定定望着,轻声道:“你哭了?”
那日之后,姬恒的话少了许多,荣蓁一直陪在他身边,不论他是何态度,都将他抱在怀中入睡,比之从前强势。
荣蓁一步步走了过去,伏在他胸前,耳边是他有力的心跳声,姬恒垂首看着她,伸手抚在她的背上,却听荣蓁问道:“你爱我吗?”
她们相守十余年,这样的话显然无需再问,可姬恒明白,她并非对此存疑,而是想要很多的爱意来驱散心头的恐慌,“爱。”
荣蓁将他抱得更紧,埋在他的怀中,她的身体微微颤抖,姬恒的手按在她后颈上,薄汗微凉浸润指尖。
“别怕。”
那晚荣蓁的脆弱真实存在,可却也只停留了一日。
而这一晚注定不平静,幼帝病情反复,陆嘉守在榻边整夜未眠,直到破晓时,幼帝的热势才退,他被邱霜扶着走出紫宸殿时,只觉脚下无力。可他刚睡下不久,又被梦魇惊醒,遍身冷汗,口中叫嚷着,邱霜从没见过他这样恐惧的神情,“主子是梦见了什么?”
陆嘉却缩到了角落里,他眼神空洞,却不停道:“不是我,我没有杀人,我没有……”
陆嘉低头看向自己双手,掌心中却满是鲜血,他大叫起来,从榻上跳下,而面前的邱霜却变作了旁人面孔,不断变换着,最后定格成韩主君的模样,厉声道:“你真的没有杀人吗?还我两个女儿的命来!”
他的脖子被“邱霜”紧紧掐住,涨红不已,气息奄奄,在他即将被淹没之时,身体却被人摇晃着,如同溺水之人被捞出水面,陆嘉倏地睁开了眼,大口歂息着,而面前正是邱霜,他分不清梦境与现实,将人狠狠推到一旁,邱霜一脸恐慌,“主子,你这是怎么了?”
陆嘉再望向自己的手时,那血迹又消失不见,他困惑着,“血呢,血呢?”
邱霜连忙让人去唤太医来,郑太医本就候在紫宸殿,很快赶来,给陆嘉施针过后,陆嘉总算平静下来,郑太医道:“太后忧思恐惧太甚,才会被噩梦所扰,臣熬些安神汤,太后服下便会好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