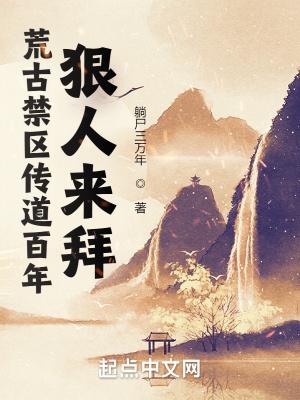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hp伏地魔x阿布 > 第8章 地窖(第2页)
第8章 地窖(第2页)
我还在香甜的睡梦中,突然就被推醒了,通过窗外稀疏的点点星光,我看到是里德尔,他半跪在我的旁边,一双大眼睛眨巴眨巴的望着我。
“肚子疼。”他的声音小到不仔细听很难听到。
我迷迷糊糊的脑袋滞空了一两秒,马上明白了,是那个蜂蜜水的问题,一股自责涌上心头,我好歹也是个大孩子了,怎么能把这点忘记了,里德尔那么瘦小,蜂蜜变质就算了,我还兑凉水喝,毒上加毒。至于我为啥没什么反应,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体质比里德尔好。
我起身摸索着,将他抱进我的怀里面,摸了摸他的额头,竟然全是冷汗。
“想不想去厕所?”我记得一般食物变质很大概率会腹泻。
怀里的他摇了摇头,柔软的丝轻轻扫在我的下颌上,有点痒。
那就好,看来并不是很严重。我双手摩擦了一下,将热的手掌心放在他的肚子上,手下是他温热的小肚子,很扁,肌肤紧绷,我还能摸到他硌手的骨头。
我轻缓的在他肚子上揉着,另一只手给他擦去额头上和脖颈上的汗珠。
一只手累了就换另一只手,祈祷着他快点好起来。
“好点了没?”
里德尔没有回话,我才现他已经在我怀里睡着了。我也实在是困的不行,刚刚一直都是闭着眼睛全凭本能在给他揉。
最后抱着他,稀里糊涂的睡着了。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里德尔已经不在我怀里了,真是个别扭的家伙。
比利·斯塔布斯这几天并不安分,他始终没有忘记他丢失的毛绒狗,他非常坚定地认为,就是某个人偷了他的毛绒狗,到了最后,演变成了他打人的“托词借口”,不少孩童因为他一句“我怀疑是你偷了我的毛绒狗”被揍了一顿。
他已经怀疑到了是我们两个偷了他的毛绒狗,虽然我义正言辞的说,是他自己在说鬼话,还是避免不了一场恶斗。
我们还是打起来了,在当天的晚餐之后。
具体细节我忘记了,当时我和里德尔端着自己的小木碗,排着队去水龙头底下冲洗。比利·斯塔布斯从后面冲了进来,不由分说的率先踹了里德尔后背一脚,里德尔踉跄了几步,摔了一跤,碗打了几个转,倒扣在灰扑扑的地面上。
我立马反应过来,一瞬间愤怒充满了全身。我用我手上的碗砸比利·斯塔布斯,可惜手滑,没砸中。最后我直接恶狠狠的扑到了比利·斯塔布斯身上,和他撕扯扭打在一起。
几个在旁边围观的比利·斯塔布斯的跟班,也一窝蜂的围了上来。
我率先出攻击,对冲上来的人又咬又踢,额头破了个洞,血流了下来糊了我一脸,牙齿也掉了一颗,我被另一个小孩按着打,里德尔被比利·斯塔布斯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情急之下,我只感觉眼前一阵黑风席卷而过过,回过神,他们已经倒在了地上。
这次恶斗最终还是被科尔夫人现了,那几个小孩仓促逃跑,撞到了路过的科尔夫人身上。最后我们几个参与打架的人都被关了紧闭,为防止我们两拨人再打起来,我们两拨人被关到了不同的地窖里。
最后那股怪异的黑风,应该就是里德尔的功劳吧,我没有多问,里德尔也没有多说。
我疼的脸上的肉冒冷汗,周身肌肉止不住的颤抖,然而眼神一转看到比利·斯塔布斯他们几个,伤口比我还惨,我就得意非常,像一个胜利者一样,高傲的抬起了我的头颅,虽然免不了又被科尔太太一顿咒骂。
最最最主要的是,里德尔被我“保护”得很好,身上只有几处淤青。一瞬间,我就觉得肉体上的痛苦也不过如此。
被科尔夫人拎着进地窖的时候,天色已经开始阴沉。
科尔夫人并没有说关多久,全看她心情,看她记不记得自己关了谁谁禁闭,不然她是很容易就忘掉的。
我还记得上一个关在这个地窖的,是一个六岁的小男孩,他直接被关了一星期,被现的时候,已经死掉了,一想到那个男孩,我心里开始毛,害怕下一秒就见到那个男孩的冤魂。
地窖暗无天日,阴暗潮湿,唯一的出口,就是那个上锁的铁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