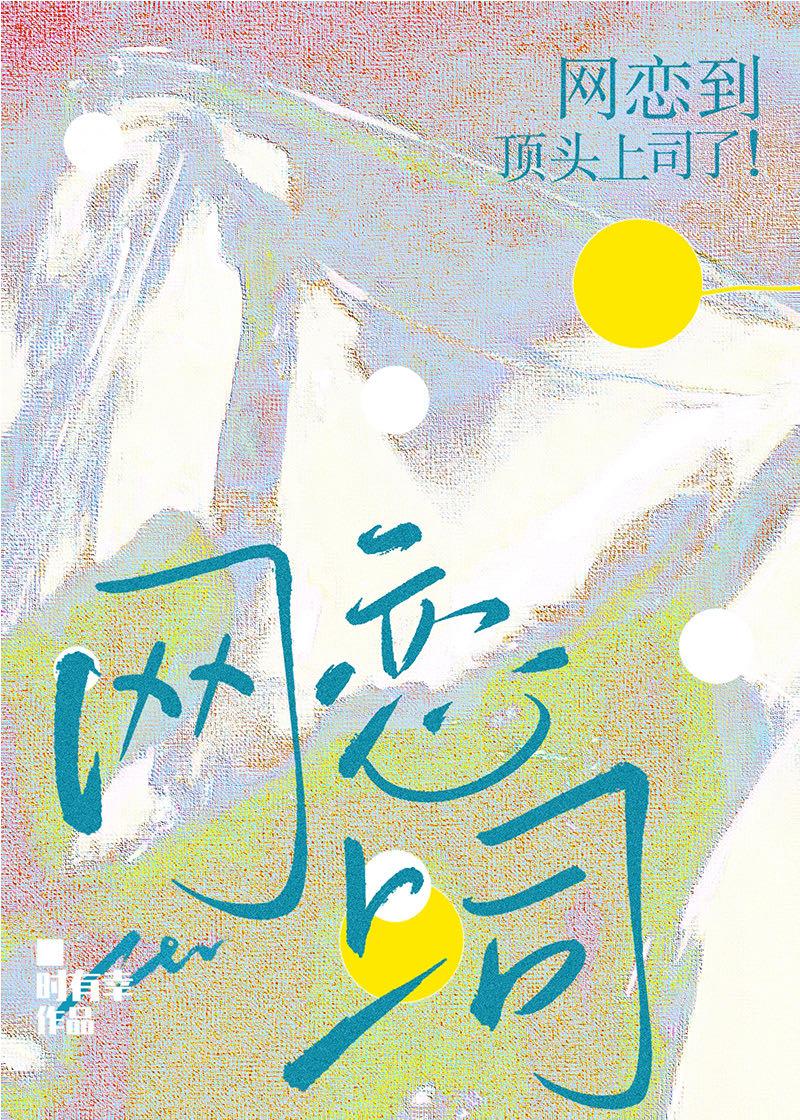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那你死在我怀里 > 昼短七(第3页)
昼短七(第3页)
直地望进唐棠的眼底,“她不喜欢喝酒。我记得她小时候闹着要我去偷师父的酒来尝尝,等我真为她偷来,却只尝了一筷尖就被辣得吐舌头,从此再也没碰过酒。”
唐棠没接这话,好像忙着跟云中任和小狼崽斗争,实则心不在焉地听着沈流云说话。
她记得这事。那是一个年节,掌门父亲很难得地取了一壶酒和两位师兄们同饮,那时唐棠和沈流云年岁尚小,自然没有他们的份。唐棠不甘心,她第一次做修真世界的任务,想尝尝这修真界的酒是什么味道,怂恿沈流云去偷酒。
沈流云拗不过她,只得去了,结果唐棠就尝了那么一点就醉了,沈流云辛辛苦苦把她抱回房间,对着那一整瓶赃物无语凝噎,最后为了毁尸灭迹不得不自己喝完,结果第二天醉得没起得来,掌门父亲上门抓人,正逮着浑身酒味睡倒在一堆的两人,气得狠狠罚了他们俩抄书半个月。
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这桩旧事,沈流云的声音里带着点笑意:“只是,我那师妹倒与仙尊一样,喜欢花。”
唐棠心不在焉地说:“喜欢花的女子并不少见,我师尊也……”
一股冷冽的梅花香打断了她的话。
三月初春,怎么会有梅花?
唐棠抬眼望去,沈流云单手掐诀,冰蓝的灵力在他的指间流转,随后凝成一支梅花模样。
沈流云握着那支梅,俯下身来。
那姿势让两人挨得极近,唐棠
一下屏住呼吸,沈流云面含笑意,神情却很郑重,他小心翼翼地,将冰蓝色的梅花别进唐棠的发间。
一瀑雪白,极称那朵梅。
“应当再有顶金冠的。”他这样说。
唐棠愣住了。
这么一件小事,沈流云竟还记得——
那日冬至,唐棠在空蝉山下摘梅插花,沈流云恰巧回来,见着唐棠,两人一起上山,她将一朵粉色的梅花别进他的金冠里。
然后她闹着要下山玩,沈流云就像以往无数次一样,就像他低下头沉默地让唐棠将不伦不类的梅花别进他的金冠里那样,那时他也沉默地跟上了唐棠下山的步子。
那日是冬至,但空蝉派迟迟没有下雪。那个冬天的第一场雪,是在太虚秘境里。
那场雪是一切的结束和开始——是唐棠的结束,是沈流云的开始。
至少唐棠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但此时此刻,唐棠看着沈流云叹息般的眼神,忽然想:真的是这样吗?
沈流云……他的人生真的开始了吗?
唐棠下意识伸出手,要把那朵冰蓝色的梅摘下来,但沈流云伸出手,覆在她的手背上,阻止了她的动作。
“师妹。”他说。这句时隔四十多年的称呼终于从他嘴里落了地,轻如尘埃,又重负千钧。他想说的或许有很多,但最后,只一花一句便足矣。
唐棠一时没能接得上话。片刻,她勉强能发出声音了,才说:“……沈剑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沈流云的
目光一沉。
他张开嘴,刚想说什么,却听得一声推门之声。
——他方才不是落了锁吗?
沈流云疑惑地看过去,只见一支翠绿的藤蔓缠在门锁上,为门外的人开了门。
白衣的男人立于门外,他含笑道:“仙尊这里好热闹啊,看来我来得不是时候。”
狐狸惯带的三分笑在黑暗中显得假惺惺的,沈流云低头,靠在唐棠膝上的云中任终于舍得支起身子,朝他露出一个冷冰冰的表情。
——谁也别好过。他用口型说。
一旁,小狼崽朝他露出两颗寒光闪闪的小虎牙。
沈流云在心里“啧”了声。
云中任就不说了,看着冷冰冰的模样,能跟时竟遥这种狐狸混在一堆的能有什么好货?一个二个的黑心肠。还有牧行之,分明是个狼模样,怎么也像只狡猾的狐狸?
“的确不是时候。”沈流云说,“时掌门现在应当可以转身离开——”
“仙尊。”时竟遥靠着门,慢悠悠地打断他的话,“我有事找。”
他强调,不忘内涵沈流云三人:“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