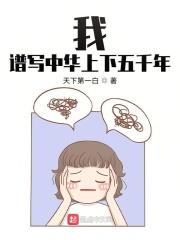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士兵突击袁许角逐1 > 第68章(第1页)
第68章(第1页)
“不想干什么。”犀牛到底忌惮张扬,没有靠近,眼神却一错不错地沾在许三多脸上,“没看见我在搭讪吗?”
张扬愣了,许三多也没反应过来,两人相视,都不懂他什么意思。
犀牛把许三多的表情收入眼中,下腹攒的火烧得更猛,他朝许三多咧嘴笑了,齿间露出一点舌头:“……小家伙,你舔过男人的x吗?”
随着他话音落下,他身后的男人们轰然大笑。
张扬眼一下子就红了,他拳头就势要打出去,被许三多拉住,后者面色青白,死死拽着张扬的手腕,对犀牛说:“下次再这么说话,我会揍你的。”
犀牛耸耸肩,很明显没放在心上。
许三多就这么抓着张扬,眼睁睁看着犀牛离开了。
他们走后,张扬把胳膊一甩,看也不看许三多,语气不太好:“你知道犀牛吗,知道他什么人吗,他盯上你了,他在猥亵你,懂不懂?”
许三多:“我不知道犀牛,但是我们走前,王组长让我们不要乱来。”
张扬抓住自己的头发,团团转了好一会儿,在牙不可能咬的更碎时,才泄愤似的往地上啐了一口。
“男人怎么能猥亵男人呢?”许三多安慰他,“他只是在挑衅我,我们小心点就是了。”
不可动摇之人
“不是!”
“不是什么?”许三多提醒他,“我们该回去了。”
张扬拉住他,许三多以为他还是对犀牛忿忿,无奈道:“张扬,王组长说了,不能擅自行动的。”
张扬的脸色很不好看,他按住许三多肩膀就往自己正脸掰:“我问你,你知道什么是猥亵吗?”
许三多想了想:“就是坏人,违背女同志的意愿,对她做、做那种事。”说到这里,他很不好意思,用袖子抹了把红了的脸,小声说:“你别让我解释了,我、我……”
“那男人呢,男的对男的……”
“男的能对男的干什么,顶多就是打一顿。”许三多自然而然地说。
张扬也是笨口拙舌,情急之下,更是上嘴唇绊下嘴唇,“不是,男的也能被……唉!”
这让他怎么说!
犀牛的事经常是组员们嘴里的谈料,就算张扬再超脱世外,也多少听说了那些奇闻,因为,看着无知无觉的许三多,他心急得不行。
眼见话说不清楚,许三多还用一种无奈又包容的目光看着他,张扬咬牙,把枪一勒,拽着许三多就走:“走,你跟我走。”
俩人简直是全速行军般回到柯加西,张扬带着许三多冲到王冉的屋子,里面空无一人,不知道他们都去哪了,他又转去找子曰,把门一推,子曰看起来也是刚回来的样子,帽沿还带着雪,见急慌慌的张扬和不明所以的许三多,随口问:“这是干什么,你们不是接活了?”
张扬把许三多一推,“犀牛盯上他了。”
子曰带着笑的脸沉了下来。
张扬出屋之后,天空是灰沉沉一片,不知何时生发了白雾,雾中隐约可见浓云攒积,远处有人对同伴喊,“天气不好,把东西收起来。”
他心情有些沉闷,快步走到王冉那里,敲门,这次里面有了人声。
“进。”是楚成峰的声音。
张扬推开门,他之前来时,还没人影的三人竟然齐全了,王冉和袁朗正坐在桌边聊天。
“犀牛?那个犀牛卖过粉,曾经因为杀人被判监禁,从美国监狱逃跑后,来到柯加西,身上背了不少命案,有消息称……”
袁朗磕着不知道从哪找来的瓜子,问:“你对这个人的印象如何?”
王冉面上露出几分厌恶:“印象不好,我怀疑这人脑子有毛病,折腾死过好几个小男孩,变态玩意儿……领导的小队叫门萨,剩下四个人也背着案底,都不是什么清白人。”
张扬一直默不作声地坐在一边,直到楚成峰注意到他,问:“任务完了?许三多呢?”
袁朗也看过来,张扬说:“在子曰那儿。”
他们继续谈话,因为天色黯淡,开了小灯,灯光下,袁朗专心致志地听着王冉的介绍,暗黄的光打在他的侧脸上,看起来很平静。
张扬心有不安,他不知道,按许三多意思不要告诉袁朗他们是否是一件好事。
他站起来,又坐下,念头盘旋了好一会儿,最终仍搁置下来,毕竟许三多说,要是他告密,他以后就不和他说话了。
子曰那边,阿陈去采购物资了,短时间内回不来,屋里只剩两人,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
许三多:“要喝点水吗?”
“哪有让客人去倒水的?”
“不要客气。”许三多憨憨地笑了笑,“蹭”地一下站起身,按子曰的指示找到暖水壶,倒了两杯水。
子曰看着他跟小蜜蜂般忙里忙外,开玩笑道:“他……他把你教导的蛮好?”
他?队长吗?
许三多没听出子曰提起“他”时的刹那不自然,给子曰递了一杯水,坐下:“队长教会我很多。”
严格讲,袁朗都是他们的老师,两人勉强能称得上“同门兄弟”,这让许三多对子曰多了很多亲切感。
子曰喝下一口水,笑了笑:“你说的对,他是个很厉害的人。”
他不想再去谈论袁朗,思绪转到犀牛的话题上,沉吟片刻,一时没想好怎么说。
他思索的档口,许三多耐心地等着,说实话,对于自己到底是怎么坐在这里的,许三多是摸不着头脑的。
张扬和子曰的神情中都有种欲言不止几乎要喷薄而出,这让敏感的许三多也意识到什么,脊背渐渐挺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