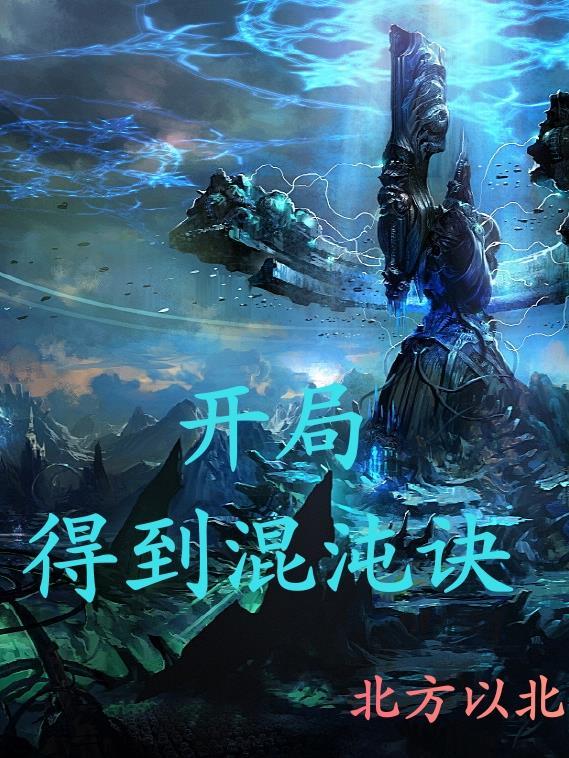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被各路疯批觊觎的笨蛋美人首页 > 第46章 叫什么秦郅玄叫老公(第2页)
第46章 叫什么秦郅玄叫老公(第2页)
“时茭,你在哪儿?你没事儿吧?”
时茭现在压根儿不敢开口,但凡他说话,时承言指定知道,他在干什么。
羞耻。
秦郅玄薄唇凑上时茭耳畔,蹭了蹭,又压抑着音量,阴森恶语:“不回答吗?”
“不回答是想要我替你回答吗?”
“你现在在哪儿?在干什么?你不说,我帮你说。”
时茭摇头。
秦郅玄眉眼凉薄,却侵略满满:“那就说话。”
时茭试探性松开自己捂住嘴巴的手,秦郅玄就使坏。
闹出了声儿。
时承言:“时茭?你怎么了?怎么不出声儿?”
又半开玩笑揶揄:“嘴巴被哪个男人堵住了?”
在秦郅玄卑劣的恐吓下,时茭也是屈服了,支支吾吾。
“在、在的。”
“你在哪儿?秦隐说他来的时候只有我,没看见你,你回家了没有?”
时茭用手挠秦郅玄,在秦郅玄脖颈处抓出几条几乎见血的痕迹。
反正秦郅玄不会还手,他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想怎么挠就怎么挠。
“你晕了、晕后,我唔……我去找人,回来你……不见了,我就走了。”
一段不能称之为话的话。
没一个字在调儿上的。
对方沉默了近乎一分钟,在时茭都以为人挂断电话了,时承言才不紧不慢开口:“你身边是谁?”
时茭:“!!!”
这么敏锐?
被现咯。
“没、没谁,就我……我自己。”
时承言是有点怀疑时茭身边有人的,可时茭说只有他一个,脑子里又蹦出来一个诡异的想法。
自己一个人,也不是不能解药哈。
时承言瞬间慌神,隔着手机,都能感受到他的窘境:“那你、你自己早点睡吧,我就不打扰你了。”
他说话也磕巴起来了。
电话刚挂断,时茭对着秦郅玄就是一通揍,巴掌都呼到秦郅玄脸上去了。
-
由于昨晚的事,时承言第二天去顶楼找了时茭一趟。
彼时的时茭,正眉目恹恹的趴在工位上补觉,脑袋枕着一个靠枕,过分饱满的粉唇微张,唇珠也艳,眉眼间满是倦怠。
时承言捏了一把时茭看起来就好捏的脸,人吐了下舌头抿唇,露出一截小舌,稍稍动了下脑袋,就继续睡了。
挺乖的。
可他眸子一瞟,看到了时茭有点泛青的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