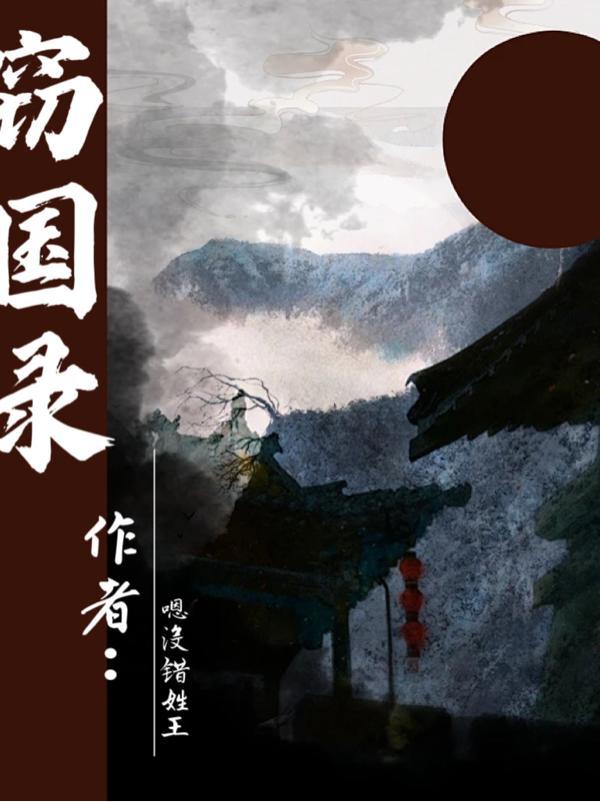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养龙 > 第33章(第1页)
第33章(第1页)
胤禩因为这场被免了随驾,很是懊恼。而胤禛胤禟胤俄此番都在随扈之列,胤禩只得想着等四哥随驾回銮之后再行解释,缓和关系。
太子被留在京中代行监国之职,每日不忘在传递邸报的同时,向皇帝阐述拳拳孺慕之情。一切仿佛都回到康熙三十年之前的父慈子孝,那一场近一年的冷落就像从未发生过。
皇帝启行之后宫中骤然冷清许多,胤禩除了上学之外就是闭门习字,偶尔去永和宫探望因病未能随驾的胤祯。
太子因为监国之故,很长一段日子没搭理他,一直到九月才又招他考校课业。长兄如父,做哥哥的考校幼弟学业无可厚非,胤禩抱了厚厚两本字帖去了毓庆宫。
太子面上露着疲色,不过倒是容光焕发得很,他见了胤禩就招呼他一道过来用茶点。
胤禩乖乖巧巧作陪,只是吃过几口奶饼之后总觉眼皮打架,神思渐渐混沌。
这是他听见耳边有太子的声音:“小八?小八?”
接着又有太监何从文尖细的声音:“八爷,太子爷还在等着您回话呐。”
胤禩抬起头目露茫然:“太子殿下恕罪,怕是臣弟昨儿习字晚了,眼下有些精力不济。”说罢更是用力曲起手指敲头。
鼻尖淡淡龙涎香一熏,正黄色的衣袂已经闪在眼前,胤禩手上一暖,吃惊抬头,握着自己手腕的可不正是太子殿下么?
“兄弟手足,你平日也唤孤一声太子哥哥,怎么如今倒生分了?莫不是听人说了什么闲话?”
胤禩急着退让闪避,难免踉跄,几步之下退在了太监何从文身上,将这奴才撞了一个仰倒。
“你这奴才,笨手笨脚的,没见着八爷困顿了,还不去偏殿收拾个榻,让八爷给歪一歪?”
“嗻。”何从文低着头迅速退下。
“太子哥哥无须……”胤禩还要拒绝,只是脚步已经不稳。眼下情形,他如何不知着了谁的道儿。只是他想不透为何太子会这样大胆,就不怕有人知道?
是了,胤禩心中突然一懔,御驾北巡,宫中自然是太子的天下。
胤禩借着脚软伏在脚踏边干呕,眼神迷茫。
太子眼中闪过鄙夷厌恶的神色,冷眼看着弟弟。
太子心道:昔日老四暂居毓庆宫时,你就同老四交好,借着老四的光入了皇父青眼。自从老四不能提携你了,你就攀上了比自己还小的老九?算得可真真清楚。孤几番召询,你都推脱装病,实在不知好歹。你既然怕露出把柄,孤就非要得你一个把柄。
胤禩急得眼泪都出来了,却偏偏什么也吐不出来,神思更是混沌。
等着药性差不多都发出来了,太子俯下身体,面露虚伪关切,却用很轻的语气说:“孤听说,你惠母妃一直拘着你不让你去阿哥所,你也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给她儿子做军师幕僚么?你这般聪明,就甘心替人做嫁衣?”
须臾间,胤禩连挪动手指的力气也没了。
何从文返回惇本殿,小声奏报太子:“殿下,偏殿已经收拾妥当了,殿下当真要?”
太子凤眼微撩,一眼斜过来:“不该问的不要问,是不是孤宠得你不知身份了?”
何从文立即低下头双肩颤抖,低眉顺目上前搀扶了胤禩往里走。
太子立在原处良久,又招来何柱儿:“你让红玉去侍候。”
红玉是毓庆宫里颇得太子喜爱的宫婢,贴身侍候太子的二等宫女。这样扎眼的人物,连何柱儿都知道怕是不好送出去。他闹不清殿下什么心思,也不敢多问,躬身下去办事。
太子当然不为收服胤禩真心,在他看来,养不熟的弟弟不如去死。
老八近日风头太盛,今次最好能得他一个弱处,日后老大兴风作浪之时,能得一个意外之喜。实在不行了,还能拖着人一起去失宠,何乐而不为?
太子盘算得好,已经开始畅想明日命人将红玉送去钟粹宫的精彩画面;畅想惠妃如何疑心暗生;畅想老大与老八如何离心;畅想惠妃不得不以老八年纪渐长之名将他送去阿哥所;畅想他日皇父归来时闻听老八得身不正如何将他冷遇。
他只用舍弃红玉一个棋子,能得到的好处实在太多。就算有人疑心他用女人引诱幼弟,只要皇父肯听他一辩,他就有本事洗脱干净。
谁知计划归计划,现实从来惹人失落让人脸红。
不过一刻,一个面貌姣美的宫女红着脸进了惇本殿。太子一愣,调笑中隐含杀机:“不是命你在偏殿伺候,怎么不去?可是舍不得孤?”
红玉低头呐呐道:“殿下恕罪,并非奴婢不去。只是八爷年纪还小……奴婢不曾……”话到这里她再说不下去,太为难了。
太子愣了好一会儿,忽然疯魔似地哈哈大笑,俯仰不已。
千般算计,从没想过这一种可能。太子与大阿哥都是十一岁刚过就有了女人,怎么会想到这个弟弟如此没用?
红玉吓得跪在地上磕头:“太子殿下饶命,是奴婢没用。”
太子却是笑出眼泪,一挥手道:“滚下去,该做什么做什么,孤亲自去瞧瞧这个老八如何年纪小。”
何从文收拾出来的屋子正是胤禛住过的知不足殿。
胤禩睡在里间床榻上,衣衫凌乱,脸上呈现出一种醉酒过后的绯红色。
太子玩惯了漂亮男孩子,本没打算对着自己亲弟弟下手,何况是自己看不上的老大一脉。只是眼前小孩情动的模样太勾人。都怪以往光顾着鄙视他,没仔细留意过。
太子走上前去,一双修长的手下意识探入被底,入手一个柔软的器官如玉一样可爱,竟然比阿尔吉善的还要干净温软。太子魔怔了似地上下滑动,很快睡着那人眉目皱起,开始细细声声喘息呻|吟,只是他隐忍惯了,那声音比小猫还弱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