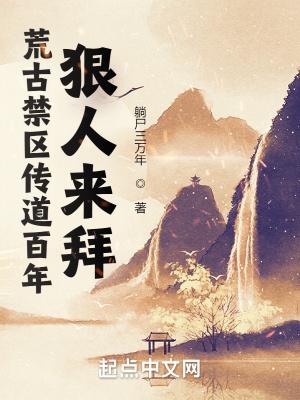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看你时自带滤镜by孟中得 > 第36頁(第1页)
第36頁(第1页)
因為和窗戶離得遠,雨雪聲聽得不太真切。
對於女主角的形象,譚幼瑾有點兒意外,完美得簡直不像一個真人。好人也不是一點兒缺點都沒有。譚幼瑾又看了一遍,發現於戡對他描寫的這個完美的人也不是很了解,像蒙了一層紗似的,像個美好的夢。因為最後沒在一起,譚幼瑾反倒不覺得假了,因為對於喜歡又沒有得到的人,總是有諸多美好的想像。尤其他這個年紀。
譚幼瑾喝完了一杯咖啡,才委婉地提了出來。因為不像於戡的路數。
「我很小就覺得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編劇好像描繪壞人要比好人順手得多,壞人很可信,好人就覺得假。我以前也這樣。」於戡突然笑,「我好像想像人的陰暗面好像容易些,簡直無師自通。」
譚幼瑾低著頭,心想所以他以前會懷疑她對他別有所圖?
「因為你,我對好人多了一點兒想像力。」
譚幼瑾沒讓驚訝露出來,笑道:「你很會誇人。」
於戡明顯對她的回答不滿意:「我像是隨時都會撒謊嗎?」
「我不是這意思,你好像只能看到我的某個角度。」拍照也是拍她最好看的一面。她低頭喝水,等水見底才說,「哪個老師那麼沒溜,天天把自己的陰暗面暴露給學生,你看到的當然都是最好的一面。」而且她那時欣賞他,當然對他好。
「那你覺得你哪裡壞?也讓我看看。」
於戡望著她,好像要發掘出她不為人知的一面。譚幼瑾站起身,去給自己的杯子舔水。水壺裡的熱水都倒完了,譚幼瑾又按了加水鍵。
聽著水流進壺裡,譚幼瑾突然笑道:「你這麼給我戴高帽子,我還哪裡敢把我不好的暴露給你。」沒等於戡回答,譚幼瑾就說:「不早了,你趕快回家休息吧。」
這是要逐客了,於戡很識地道別,跟譚幼瑾說明天見。他走得太迅,連外套都忘了拿。等他出了門,熱水壺裡的水開了,譚幼瑾才想起他的外套搭在衣架上,雨傘也沒拿。
等她走到電梯,電梯顯示在一層。她馬上給於戡打電話,讓他在樓下等她。
於戡並沒在電梯口等她。譚幼瑾走到單元樓門口,才看到於戡,他身上又被打濕了。這人走得可太快了。
「你沒打車嗎?」
「這天不好打車,騎車過去也沒多遠。」於戡看到譚幼瑾手裡的黑傘,問,「要不要出來看看?」
就在譚幼瑾猶豫的當兒,於戡已經把單元門打開,順走了她手裡的傘,砰的一聲傘打開,於戡在門外等著譚幼瑾出來。
「今天不看,明天晚上就看不到了。」
譚幼瑾和於戡不一樣,這些年看見過許多次雪,然而她也被他的興奮感染了,自動走到了傘下。
傘下只有她一個人,譚幼瑾說:「現在不是白天,你還是進來躲會兒吧。」
雨夾雪落在地上,很快結成了冰。
「又不是夏天的暴雨,落在身上簡直沒有感覺,而且我有帽子。」他的家鄉冬天時常下雨,而這種淅淅瀝瀝的雨天,他從不帶傘。偶爾錯估了雨勢,雨下得比他想像得大,有人邀請他共打一把傘,他也從來都是拒絕。兩個人打一把傘的結果,就是兩人都會淋雨,倒不如一個人獨自打。
譚幼瑾心裡笑他幼稚:「你以前也從來都不打傘嗎?」
「除非雨下得太大。」於戡笑道,「但是雨太大,傘的作用也有限。」有段時間他父親來北方發展,他臨時和他母親同住,是八月份,一次遇到大雨天,他倒帶了傘,可惜傘骨被刮折了,避了一會兒雨發現雨量並沒有減少的趨勢,只好冒雨往回走,整個人被暴雨洗了一遍,回到他母親的房子帶了一身的雨水,其他人正在吃飯,最先注意到他的是保姆,看見他讓雨水淌進了家裡,小聲抱怨道:「真麻煩,一會兒還得收拾。」他當然也沒有為此覺得抱歉,反而像一條狗似的抖落自己身上的雨,地板上更髒了。他對著地板笑,惡作劇得逞的那種笑容。沒幾天,他就搬走住校了。他又花錢買了一把雨傘,雨傘很結實。
四周的白都摻了顏色,白得一點兒都不純粹,和上次的大雪完全不一樣。上次腳踩在地面上,還有咯吱咯吱的響聲,這次則悄沒聲的。腳下的雪已經被行人的腳印踩實了,硬梆梆的,一不小心就有滑倒的風險,她仔細盯著地面,路燈的光映在摻著灰色的雪面上,一步步都走得很小心。她注意到於戡的鞋子,他好像把家鄉的習慣一直帶到了這裡,從來沒穿過棉鞋。突然她注意到於戡的鞋面和地面打滑,下意識地用手抓他的胳膊。
譚幼瑾嘴裡的「小心」剛出口,於戡的腳已經穩穩地走在路面上。她把手忙縮回口袋裡,解釋道:「我以為你剛才要滑倒了。」
「你走路這么小心,很怕滑倒嗎?」
怕滑倒怕骨折怕一切意外,當然現在好一些,如果真滑倒扭傷了,實在麻煩可以請護工,不用麻煩母親。她小時候懼怕一切有風險的事,一半是因為真出了事後果要她母親承擔,她自己承擔不了。她這一點倒是像她母親,周主任做事風風火火,但在健康上卻是很小心,因為真有了意外,丈夫不能回來,家裡非但沒有人可以依靠,還有一個孩子要依靠她。
譚幼瑾懷疑自己對風險的厭惡在幼時就已經生成了,她反問道:「你不怕嗎?」
Tips: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或推薦給朋友哦~拜託啦(。&1t;)
&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