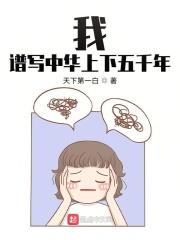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洞房前还有遗言吗全文免费阅读 > 第五十九章 在皇帝面前秀恩爱(第3页)
第五十九章 在皇帝面前秀恩爱(第3页)
门响,有公公给开了门,附耳听得外边小太监传来的消息,随即示意他稍等,然后朝皇帝走去,“陛下,昱阳郡主领着世子来探望皇后娘娘。娘娘唤您过去呢。”
卿如是眸光微亮,稍抬了抬眸,偷觑那公公,无意扫到皇帝,这才真正窥见天颜。方才她一直埋头不敢直视,竟不知皇帝的长相并不似他的声音那般洪亮,皇帝阴柔且俊美。
她正瞧着,那双阴鸷的眸子忽地与她相接。猛一吓,卿如是立即低头俯身,这才回味着公公的话。
月陇西来了。他在画舫时的确说过,前些时候皇后娘娘体乏病了,郡主去探望过。可,分明不久之前月陇西还在城楼和她玩耍,这么快就回了月府,跟着郡主又来探望皇后?
正想着,又听那公公低声道,“世子他……带了一只白鸽来。”
卿如是听得一怔,眉心微跳了跳。这么巧?难道是她方才让他转告父亲若能进宫定要带白鸽来,所以月陇西便接过这活,从父亲手中把白鸽带了进来?否则……他怎会这么碰巧,关键时候将鸽子带来呢?
她的心忽然忒忒地落不安稳。也不知月陇西带来的,是不是从她房中拿走的那只?或者,那只白鸽足底有没有信?只带白鸽,不带信来,那还不是空跑一趟?
皇帝听后也不知是何神情,卿如是不敢再看,只知他沉吟许久,低问了句,“你腰间的牌子,是陇西的?”他是说瞧着眼熟。
这回虽没加称谓,卿如是却知道是在跟她说,立即颔,谨慎回,“是。入宫之前,世子正带着臣女在城楼玩耍,侍卫找到臣女并说明情况后,世子便将这玉牌给了臣女。”她一顿,又有些担心皇帝怪怨她私自收下这令信,便补充道,“若……欠缺妥当,臣女立刻便将令信归还世子!”
“嗤,令信?”
轻呵气声入耳,卿如是不确定,皇帝竟笑了?
她有些紧张,生怕这是怒极反笑,赶忙自作主张将腰间的玉牌取下来,双手奉上,“还请陛下去时捎带上,交还于世子。”
皇帝不答,卿如是一颗心便又提到了嗓子眼。明明局势已经在她掌控中,此时月陇西来了,反倒让她坐立不安。
这玉牌究竟什么意思,陛下是在考验她?还是在吓唬她?或者,晟朝有规定,令信是不能给人的吗?诸多猜测,卿如是脑袋上的闷汗憋了一晚终于落下来了。
片刻后,皇帝示意身旁的公公拿走她手中的玉牌,“都跟着。”
皇帝拂袖起身,绕过卿如是往门外走,留下这般令人匪夷所思的话。卿如是没时间多加揣度,在太监的催促下起身跟了上去。
饶是周遭风景再如何秀丽,卿如是也不敢抬头去看,只听到有夜巡队的脚步声,和遥遥的蛙声蝉鸣。宫人提着琉璃瓦灯,前开道,后追随。
她的眼前明明闪闪,心也跟着忐忑。
皇帝倒是乘坐软轿,卿如是刚跪了许久,却还须得跟着走。也不知过了多久,坤宁宫到了。有太监腿快,跑进去禀报。
月世德被皇帝抬手示意,阻于坤宁宫外,只得俯跪在地等候。卿如是跟在身后,心以为自己能进去见到月陇西,一窥那白鸽究竟。却在入殿门时也被拦于门外。
她微微垂着眼睫,恭顺地朝殿内的方向行跪拜之礼,而后伏在地上不动了。眼睁睁看着殿门打开,一瞬的欢声笑语入耳,皇帝入内后,殿门又瞬间合上,阻断了话语。
皇帝进门,先看向了月陇西。
他正悠然逗弄着腕上的白鸽,唇畔噙着从容的笑,自在地给它喂食。见到皇帝后,随着几人一道起身施礼,却没有坐下,站在那里,静等皇帝说话。
皇帝瞥了眼身旁公公,示意他将白鸽拿来。月陇西浅笑着,只在白鸽的脚腕上抽出一张信笺递过去。
“姨父,这信是孩儿写的。”月陇西笑吟吟道,“与她闹着玩呢。”
月陇西在皇帝面前耍赖时,惯是只把他当亲戚唤,自幼皇帝喜爱他,从来都随他去。
皇帝却不与他说笑,肃然问,“这字?”
“自然是孩儿仿照着秦卿的笔迹学来玩的。”月陇西示意公公磨墨,“您若不信,孩儿可以当场写几个秦卿的簪花小楷给您瞧瞧。”
说着,他当真动手写了几个字,让公公拿去给皇帝过目。
皇帝接过,随意瞟了眼。却并不说话。
就听月陇西接着道,“前几日长老为难她的事孩儿也听说了,便猜到今日姨父召见她是长老在饶舌,搅弄是非,故而,特意来跟您坦白。方才却听姨母说起宴会之上,长老要呈给您看的东西无故变成了女帝手札之事,还说手札末尾的字迹像是秦卿的簪花小楷。事关重大,姨父可得好生介入调查,若长老他真有叛族之嫌,月府也绝不会包庇的。想来调查此事必定繁琐,姨父便莫要为了孩儿的一时顽劣再分心神去为难卿卿了。”
原本还听得好好地,到此处,皇帝冷嗤了声,“卿……什么?你再说一遍?”
月陇西垂眸笑。
皇帝抬手,身后的公公将刚从卿如是那里缴来的玉牌递到他手中,他摩挲着玉牌,看见月陇西绷了一晚的从容神色终于有了几分改变,他终是心满意足地抿了抿唇角,将玉牌丢给月陇西。
“死乞白赖从朕手里要的,却被人当作令信,毫不留情地还回来。你混得可真不怎么样。”
月陇西怔怔地,讷然须臾,皱眉问道,“陛下,她人呢?”
“哦。”皇帝又垂眸瞥了眼纸笺,轻描淡写地道,“朕下令杀了,血溅御书房,刚命人收拾。你若现在赶去看,尸。体兴许还在。”
。&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