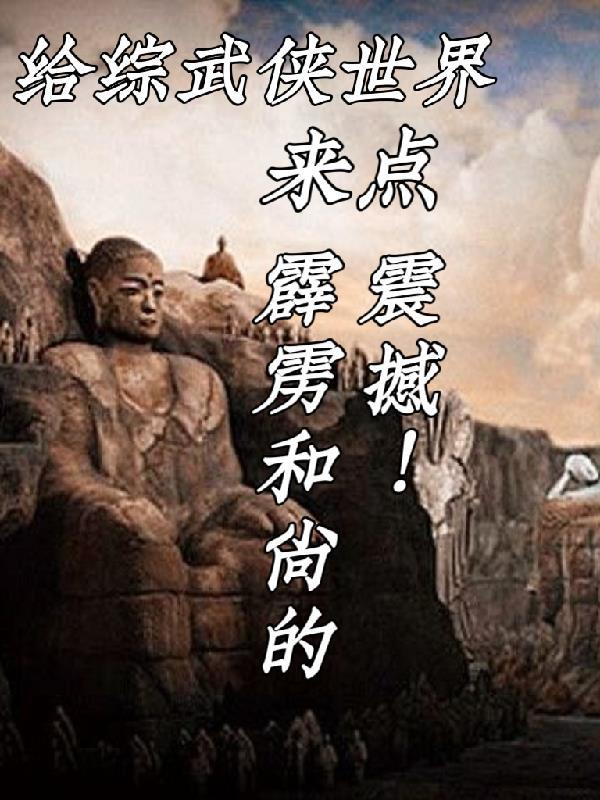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美人谋国 > 第90章 蒙山(第2页)
第90章 蒙山(第2页)
她的声音很平稳,神情平静,没有其他类似于愤慨或是怜悯的情绪。
萧澈吃惊。
却是吃惊此事被孟晏云知晓。
并更疑惑:“你便是因此事这么多日不理会孤?”
孟晏云心略稳了稳,伸手紧紧握住萧澈的手。
“其二,太子妃伙同齐王,在殿下熏衣物的香料上动了手脚,令殿下子嗣有碍。”
萧澈的脸色一开始还镇定着,可是越想,他便越是心惊,越是觉得不敢置信。
他的手紧握成拳,青筋暴起。
每半个月太医都请平安脉,却是没有一人告诉他此事……
那会不会,此事就是太医都看不出来的呢?
“孤这就回京召集太医院会诊!”
他猛然起身,往外大步走去。
孟晏云依旧跪在原地,没有阻止。
萧澈走到门口,再没有往外跨一步。
为什么?
他知道父皇猜忌他,不喜他,可再怎么说父皇还是立了他做太子。
他以为,他们之间至少还存有那么一丝父子之情。
父皇可以敲打他,可以给他试炼,他还有那么多兄弟,那么大的江山,父皇不仅是他的父亲,还是皇帝。
制衡朝堂,权衡利弊,应该的。
可父皇这是完全没有要将江山交给他的打算。
就凭不能有子嗣这一点,他便是才能再出众,后继无人,他再无登基的可能。
“哈哈哈……”
他扶着门框笑了起来,笑声悲怆癫狂。
孟晏云缓缓起身,走到萧澈身边,轻声说:“臣妾让父亲暗中从云州请了大夫来,大夫此时就在山上,挺凭殿下吩咐。”
说完,她安静的站着,没有说安慰的话。
事实如此,她再多安慰的话都是无济于事。
萧澈深吸一口气,再转身时,已经恢复平日冷静沉肃的模样。
他走回椅子处坐下,声音低沉:“宣。”
孟晏云示意秋白去将人带进来。
一个身穿铠甲的青年眉眼低垂的走了进来。
他拿出脉诊,躬身在萧澈身边。
等萧澈伸出手腕,他搭上萧澈的脉门。
屋子里安静下来,静到几乎能听到几人的呼吸心跳。
孟晏云的心也提了起来。
上一世姐姐曾经有过萧澈的孩子,她相信姐姐不会做不该做的事,那便是说明萧澈的身子或许并非有坏到底。
但从姐姐孩子流掉之后,就再也没有喜讯。
所以她也不能确定萧澈的身体还能不能医治。
过了好一会儿,青年收回把脉的手,说:“殿下肾中阳气亏虚,所以子嗣艰难,不过尚有解决之策,并无大碍。”
闻言孟晏云总算放下心。
“谢先生,请先生先下去休息。”她含笑对青年道。
“娘娘客气。”
青年眉眼始终没有抬一下,安静走了出去。
屋子里又只剩下孟晏云和萧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