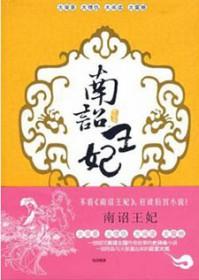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县太爷的故事 > 第6章 快下山去(第1页)
第6章 快下山去(第1页)
原榭慢慢清醒过来,离开了那种浓郁的香味,他身体上的麻痹也渐渐消失,想起刚刚的事情,他忍不住面红耳赤:“多谢大当家。”
“明日一早赶紧下山,这土匪窝不是你能呆的地方。”
“不!我还没待够!”
“你!你就想跟翟玉卿睡一次才罢休吗?”
“不是,我还有些疑问没查清,不能走。”
“查什么?你问,问完明天就走!”孔令玄倒了杯茶,一口饮尽。
“你为什么要绑架齐家二公子?”
孔令玄沉默:“……”
“大当家若是不说,我是不会离开的。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想让我走,就给我满意的答案。”
“他自己花钱让我在婚礼当天把他绑走。”
“什么?”原榭显然不相信这么荒唐的答案。
“三天前的一个晚上,齐汝城蒙着脸偷偷上山,带了三千两银子,说只要在婚礼当天我们把他绑走,就把钱给我们。他不想娶叶家小姐,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不得不娶。”孔令玄面无表情地说道。
原榭结合白天婚礼上齐汝城的表现,确实不像一个想结婚的人,拜堂像木偶,土匪来的时候他跑得最快,把新娘子一个人丢在礼堂上。
孔令玄从怀里摸出一张纸:“生意上门,有钱必做。”
原榭拿过孔令玄递过来的纸,这是一张契约,上面写着的就是齐汝城跟孔令玄的交易,齐汝城花三千两银子让土匪在婚礼当天把自己绑走。底下还有两人按压的手印,旁边写着:言必信,行必果,公平买卖,童叟无欺。
败家子!原榭看完之后对齐汝城就三个字的评价。
“事情已经告诉你了,明日可以走了吧?”
“不,你们寨子我还没看完呢!难得来一次,你明日带我去走走,看完我就走。”
“你!”孔令玄攥紧拳头砸在桌上,把桌面的茶杯和油灯震得跳起来。他压下了自己的怒气,“看完就走?”
“看完就走!”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成交。”孔令玄脱了靴子和外衣,躺在床上,他已经奔波了一天,实在没有任何力气再跟这位县太爷扯皮,纯属浪费力气。
“大当家的,那我呢?我睡哪儿?”
“地上。”
“大当家的,这可不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啊!我好好的在山下,你们这些人非要把我绑到山上,却又让我睡地上,实在无礼。不如我去找二当家?可是他似乎热情过度……”
在他的一番唠叨之下,孔令玄往床里面挪了一个位置。
原榭躺在了空位上,目光看到了穿洞的屋顶,下雨的时候肯定会漏水。“大当家的,你生活得还挺艰苦的,这屋可是时常漏水?”
……对方没有回答他。
他又侧脸看着孔令玄,对方带着面具,上半张脸遮住了,露出下半张脸,双唇红润,不算薄,是个厚道仁义的人。“大当家的,大晚上了,还戴着面具?”
……对方也没有理他。
“莫不是你脸受伤?还是你觉得自己长得太丑?还是你是……通缉犯?”对方的呼吸很轻,很平缓,他以为对方睡着了,于是抬手想要把对方的面具拿下来。
在刚碰到面具的瞬间,他的手腕就被人钳住了,一股很强的力量让他动弹不得。随后对方推开他的手:“大人,不该管的不要管,不该看的不要看,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
原榭悻悻地收回手,安安分分地躺在旁边,对方虽然跟屠一刀和翟玉卿是土匪,但有自己的原则,他不会像屠一刀一样天真鲁莽,也不会像翟玉卿一样放浪形骸。
他虽然可以忍,但踩到底线,很容易反噬。原榭觉得这人像一只老虎,收起爪子的老虎。
*
清晨,树林传来的鸟叫声阵阵,太阳穿过树林照亮了平乐寨,也照在了原榭身上。寨子里养的鸡扑腾着翅膀飞到草垛上“喔喔喔”地叫起来。
原榭揉揉眼睛,说实话,他已经很久没有睡到自然醒了。他扭头,躺在床边的人已经不在了,至于什么时候起来的,他也不知道。也许是昨晚太累了,他睡得很沉,也有可能是翟玉卿屋里的迷药药效太强。
他从床上爬起来,桌面放着三个窝窝头,估计是孔令玄吃剩下的。他那拿起一个,放在嘴里咬了一口。门外传来练剑的霍霍声。
他打开门,孔令玄在院子中练剑,三尺青锋左右连续剑,剑气逼人,一个飞身回旋剑像龙卷风一样激起了空气震荡,就算是距离十丈远的人也能感受到剑气的锋芒,身上穿着单薄的中衣。
原榭忽而意识到,这人绝对不简单,他到底是谁?为何要戴着面具?
大约舞了三刻钟,孔令玄也收了剑,满头大汗,中衣也被汗水浸湿了。原榭吃完了馒头,朝他打了个招呼:“大当家的,好身手!”
孔令玄没有理他,越过他径直朝屋里走,他拿起挂在架子上的布,在脖子上、太阳穴附近擦汗,动作利落干脆,跟以往每天必做的程序一样。他解开中衣,准备换衣服。
跟在他后面进来的原榭看到了他后背,他背部到处是伤痕,没有一寸完好的皮肤,在肩胛骨下方缠着一圈纱布。虽然已经愈合了,但剩下的疤特别明显,有深有浅,从形状上看,有鞭子伤,有刀伤,有热水烫伤的,有钉子伤,有箭伤……
他意识到有陌生人在背后,褪到腰部的衣服瞬间又穿好,他没有回头,冷冷地下命令:“出去,把门带上。”
原榭没有多问,十分配合地离开屋子,顺便把门带上,但是那个布满伤疤的背部,却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知道上面的大部分的伤都是监牢里的刑具留下的,小县衙可没有这么多的刑具,大部分刑具都在大理寺。他曾去过朝廷的大理寺,知道那里是怎样对待犯人的。这是得犯了多大的罪,才会受这么多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