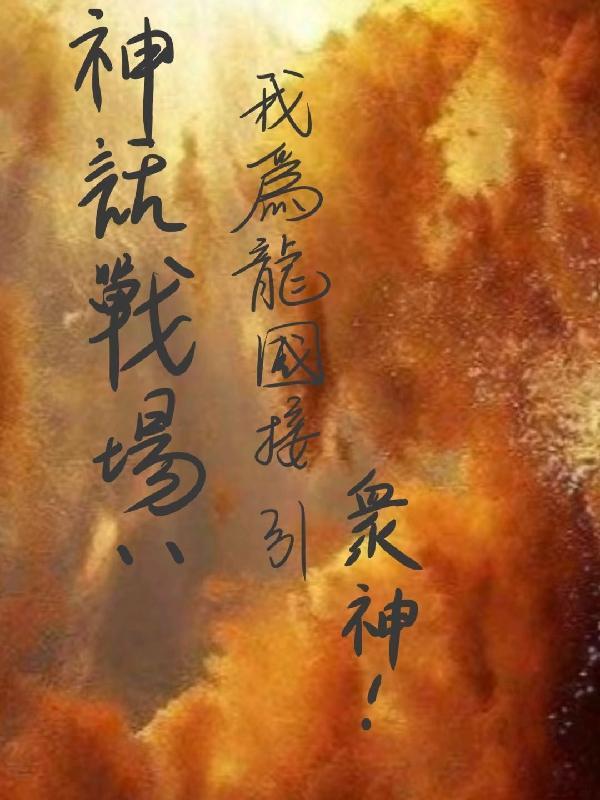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并不想加入主角团txt > 第19頁(第1页)
第19頁(第1页)
我就自己吃起來。
邊吃邊跟他聊天,讓他弄完這盆羊肉就差不多了,別搞那麼多,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他說大部分都不是給我倆吃的,是供奉給祖先的。
我心想你都出身不詳了哪來祖先,你不知道你祖先是誰,你祖先估計
也不知道你在哪兒。
但這話太沒禮貌了,我就沒說。
就在這個時候,不之客來了:「你們這是……」
樓起笙理都沒理,只有我給面子地轉頭看著秀才哥,還客氣地打手勢叫了一聲人。
其實我也不想搭理他,但被社會狠狠操過的我足夠虛偽。
這就是我和還在長牙的樓起笙的差別了。
我,在心靈上已經是一個相對成熟的能屈能伸社會人了。
所謂能屈能伸,說穿了就是熟練當烏龜。
哪怕前一天我倆互掐脖子互罵娘,第二天就因為總還是要低頭不見抬頭見而當昨天無事發生,笑著說早上好啊吃了嗎。
這是社會人的奧義。
社會人固然可笑可悲,令人不得不如此人不人鬼不鬼的社會才是罪魁禍。
秀才哥的眼神看起來很是微妙,半晌,道:「雁,你當真要如此胡鬧?」
你是不是有病?你就說你是不是有病?
不是你把我逼到這份兒上嗎?現在五百兩你都拿了你又來說這話?是不是精神分裂啊你?
但我是社會人,我不能這麼直說。
我只能高情商地裝沒聽見,然後比劃著名問他來幹什麼。
他說:「我們思來想去,還是覺得——」
他話還沒說完,樓起笙頭也不抬地冷冷道:「再多嘴,殺了你。」
秀才哥:「……」
為息事寧人,我忙圓場跟秀才哥說是開玩笑的。
秀才哥看看我,看看樓起笙,再看我,給我使眼色示意我看樓起笙,表情看起來就像是在說:你自己看他是不是在開玩笑的樣子。
我真看了一眼樓起笙,小伙兒也看向我,表情寫著:那孫子好煩人啊,不想跟他玩。
我回他一個「你放心,我肯定不跟他玩只跟你玩」的安撫性眼神。
然後肯定地跟秀才哥說真的是開玩笑,不過既然你開不起玩笑,那我們就不跟你開了。
說了我是社會人。
社會人常用的先開個一點也不好笑的冒犯性笑話然後你生氣就倒打一耙說你開不起玩笑那就不開啦……這種心眼子我也會使。
秀才
哥有被噁心到,嘴角微微抽搐了兩下。
但他及時忍住了,目光從樓起笙豐富的備菜上掃過,露出些許貪婪想要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