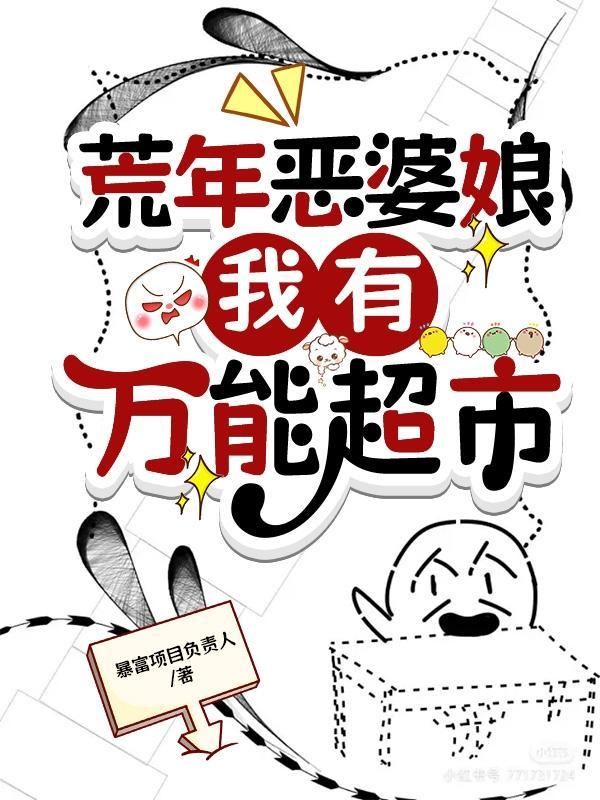残月轩小说网>锁南枝傻俊角 > 第118章 惩罚(第1页)
第118章 惩罚(第1页)
敲门声响起,江映林方才回过神来,她抽出手来,起身去开门,是卫风端了熬好了的药来。
“有劳姑娘了。”卫风将药递给江映林,江映林点点头,端着药回到榻前。
“哪里来的药?”秦恪野闻到药味,忍不住捂了鼻子。
“我料定若非我盯着,这药你怕是吃不到嘴里,故而我来之前专门去找了坐堂先生,把你的情况跟人说了说,抓了药,都给你带来了。”江映林手拿瓷勺,舀了一勺,搁在唇边吹凉了,来喂秦恪野。
秦恪野屏息往后躲,又准备来撒娇讨饶:“绵绵……”
“这次不论说什么,这药都得喝。”江映林硬起心肠来:“若是你不肯喝药,以后你也别来见我了,东侧的窗子,回去我便叫下人封了。”
“喝,我喝……”秦恪野接过江映林手里的碗,嘴唇试了一下温度,温热的正好。秦恪野小心翼翼地又拿舌尖沾了一下,顿时苦得脸都皱在一起。
不由得又看向江映林,江映林根本不看他,秦恪野咬了咬牙,心一横,端到嘴边咕咚咕咚地饮了,苦得头皮都麻。好不容易放下了碗,江映林却凑上前来,捏着秦恪野的嘴巴,放了一颗蜜饯。
“好些了吗?”江映林终于带了笑。
蜜饯的甜腻和药的苦涩混在一起,滋味算不得好受,秦恪野起了坏心思,又将江映林拉回来,含糊的说道:“你自己来尝尝?”
一颗蜜饯,混着药香。从一个唇齿间滑到另一个唇齿间。
“你比蜜饯甜。”秦恪野得了便宜不忘卖个乖。
江映林嘴里含着蜜饯,吐也不是,咽也不是。几经挣扎,还是慢慢了咬了,咽了下去,却又不知又哪里惹了秦恪野,这人的眼神又不对了。
“喝了药,便早些休息,好得快些。”江映林又扶着他重新趴下。
“那你呢?”秦恪野趴下了,又抬起身子,不放心地问。“时辰已经不早了,我过一会儿就得走了。”江映林看了看窗外的天色,道。
“我送你。”秦恪野说着便要起身。江映林连忙将人拦下:“你好生地歇着吧,有卫风送我,你若是不肯听我的,我以后便再也不来了。”
秦恪野犹豫了一下,又重新趴了回去:“依你便是,你跟卫风说,南苑前头的那条路在翻新,晚上看不清,就别从那条路走了,往西边绕一圈,虽说是远了一些,毕竟安全些,我也好放心。”
“知道了。”江映林点点头。
秦恪野拉住江映林软嫩的小手,有些不舍,他睁着眼看着她半晌,不肯好好睡下,可那药效来得也快,眼皮渐渐有些撑不住。
江映林等了一会儿,轻轻把手抽了出来,尽管动作已经够轻,秦恪野还是惊醒了,他似乎是受了惊吓,眼睛瞪着,攥着江映林的手不由得收紧,江映林轻轻拍着他,哄孩子般的安抚:“没事,没事,我在呢,睡吧睡吧……”
好一会儿,秦恪野才又重新闭上眼,半梦半醒之间,嘴里嘟嘟囔囔的:“绵绵,你等等我……再等等我……”
江映林趴在他的唇边听了个大概,心里头像是游进来一尾鱼,在她化成一汪水的心里,轻巧又敏捷的在里头搅啊搅的,她低头吻上秦恪野耳下那颗妖冶的痣:“我等你……”
等卫风将人送回江府的时候,已经过了子时,江映林带着绒葵从原路回到院子里,却现卧室里的灯却亮着。
“姑娘走的时候没熄灯吗?”绒葵有些不安道。
江映林走得匆忙,此时想起来,也一时不敢确定,主仆在门外二人对视半晌,江映林颤抖着手推开门,就看见江夫人就坐在里头!
江映林心下一凉,不由得咽了咽口水。脑中飞快地不断想着各种借口,却在江夫人的目光中,她终于想起来此前忽略的一件事。那在小厨房后面嚼舌根的杜鹃,是她母亲院里的丫头!
江映林站在门口,连迈进屋子的勇气都没有,颤巍巍地唤了一声:“母亲……”
“去哪了?”江夫人盯着江映林,目光平静,却像是要在她身上盯出一个洞似的。
江映林在夜里后背都一层汗,自小她最怕母亲这样,她越是平静,后果越是严重。江映林在天人交战中不知怎么就想起来秦恪野迷迷糊糊之间,拉着她的手,叫她再等等他……他捅破了天,挨了那样一顿打,践行他的承诺,她如何能退?
“母亲不是都知道了吗?”江映林咬咬牙,抬起头来。
“什么时候开始的?”江映林的话出乎江夫人的预料,她面色更沉,声音不自觉地加重。
“金家的马球会。”江映林道。
“好好好,你倒是认得干脆!”江夫人站起身来:“我道那秦恪野怎的就敢突然上门,对你父亲说那样一番话,原来你们……你们……”
剩下的话江夫人说不出口了。她原只是疑心,略施小计,不想却逮了个正着。
“母亲!”江映林在门外跪了下去:“求母亲成全!”
江夫人没有料想听到这么一句话,心头的火烧得更旺,她伸手抓过桌上的茶杯砸了下去,清脆地一声响,茶盏里还没有喝完,剩下的茶水,屋里的地面立刻湿了一片。
“简直痴心妄想!”江夫人厉声道:“秦恪野在你父亲那使了苦肉计,你便有样学样了吗?你喜欢跪,便去祠堂跪上三天,莫在我面前碍眼!”
江夫人侧过身去,根本看也不看江映林:“那秦家是什么家世?你对他们家的事又知道几分?就敢大言不惭地叫我成全?可笑至极,这事不若说过不了你父亲那一关,便是我这,也是万万不可能!
看来是我们往日里对你太过骄纵,惯得你不知天高地厚了!从今日起,你就待在府里思过,每隔三日跪一日祠堂,没有我的吩咐,不得踏出府宅一步!”
江夫人说完便拂袖而去,江映林去抓她的裙摆,却扑了个空。
江映林被禁了足,搬离了芙蓉院,住在她母亲院子里的偏院里。晨昏定省,白日里抄书,每隔三日去跪一日祠堂,膝盖都青紫一片。这回,她一点软都不肯服了,母亲罚她,她认罚,可若是叫她认错,她绝不肯了。
芙蓉院东侧的窗户被封了起来,秦恪野好了以后,避着人来看她,只是那窗子,再如何敲,也不见人来开了。